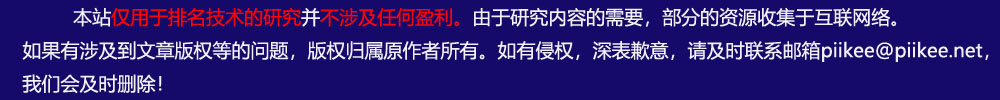神武手游可以在电脑上玩吗(神武手游怎么解绑手机)
梦幻诛仙手游ios怎么在电脑上玩?这一直都是玩家关注的焦点,梦幻诛仙手游作为大型RPG手机游戏,在手机上操作运行都是需要较高配置支撑的。那么还有不少玩家还对梦幻诛仙手游ios怎么在电脑上玩还不是很清楚,接下来就和琵琶网小苹果一起来看看吧,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最新版本:
ps:下载注册即可参与独家活动,新手豪华礼包免费领,充值返利活动!
梦幻诛仙手游电脑版
梦幻诛仙手游ios怎么在电脑上玩?
1、不能是模拟器,目前如何模拟器都不能模拟苹果系统,所以一些小伙伴不要相信所谓的IOS模拟器
2、手游的PC版,这个是官方出的,一般也不能运行IOS的,但是有的能,如神武梦幻西游的Ios有pc版。
3、目前梦幻诛仙的PC下架了,在TGP、腾讯游戏中心等都不能下载PC版,后续官方也许能开发出IOS的电脑版。
所以就目前而言,IOS的苹果用户不要想在电脑上玩,现在至少是不行的。
至于什么梦幻诛仙主播怎么在电脑上玩啊,你们在主播那看到的只是苹果录屏大师,把手机的影像转到电脑给你们看罢了,实质上还是在手机上完。只是主播方便给你们观众看罢了。
欢迎玩家下载梦幻诛仙手游安卓ios客户端,只需要在百度输入【梦幻诛仙手游琵琶网】就可以直接下载安装包,看手游攻略,请认准梦幻诛仙手游琵琶网专区。
梦幻诛仙手游玩家交流群,职业加点,礼包领取【下载梦幻诛仙】或【进群讨论游戏技巧】
本文原刊于《宋史研究论丛》第22辑(2018年)
感谢李小霞老师赐稿!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 要:割地父事契丹,置十六州土地百姓于化外之地而不顾,成为历来评价石敬瑭无法脱离的历史事实,以往研究也多将燕云十六州笼统地划分为赵德钧所控制的幽州诸地与石敬瑭所辖河东诸州两部分,然通过对五代尤其是后唐政区地理沿革的史料爬梳与分析,燕云诸州按照其实际控制权可划分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所领幽、涿、蓟、檀、顺、瀛、莫七州,新州威塞军节度使所领新、妫、儒、武四州以及雁门关以北的云、应、朔、寰、蔚五州三大部分。在中原内部诸方势力争斗日趋激烈的历史前提下,困守太原、形势蹙危的石敬瑭在多方考量之下,选择出让赵德钧的全部利益、后唐李从珂的部分权益以及自己的少许利益即蔚州一地作为坚定契丹盟约的交换条件。石敬瑭割地事辽之举,并非草然决定,而是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下作出的政治取舍,既是中原内部权力角逐下排除异己敌对势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在生死存亡之际全力确保契丹南下援助的决定性筹码。
关键词:五代;石敬瑭;赵德钧;辽太宗;燕云十六州
作者简介:李小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代后唐清泰三年(936)五月中原再度爆发内乱,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自立,以割地称臣、厚与金帛、父礼事之的重赂求得契丹援助,在耶律德光五万铁骑的强力增援下,石敬瑭一举攻入洛阳,唐末帝李从珂举族自焚于元武楼,开启五代历史上又一王朝统治时期——后晋。在石氏求援契丹的诸项条约中,割让燕云十六州一事影响最为深远,其后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鼎峙而立的历史格局的形成与之便有着莫大的关系。学界对于燕云十六州这一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在石晋割地的历史评价、燕云十六州与宋辽关系、辽属燕云的历史作用与地理沿革等方面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石敬瑭割地一事本身的关注较少,如石敬瑭为何单单选择割让燕云十六州作为邀约契丹南下的筹码而非其他地区,这与中原的政治形势以及石敬瑭的处境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在割地之际石敬瑭又有着怎样的权衡思量等问题,似还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空间。[2]有鉴于此,本文试以燕云十六州的实际控制权为切入点,结合五代时期中原纷争形势以剖析石敬瑭割地之际的政治考量,以期能为石晋割地事辽一事提供另一认知视角,挂一漏万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燕云十六州,是后世对石敬瑭所割让十六州之地的专有称谓,包括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蔚州(今河北蔚县)、幽州(今北京)、涿州(今河北涿州)、蓟州(今天津蓟县)、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儒州(今北京延庆)以及武州(今河北宣化)。关于十六州在后唐末帝时期的政区归属问题,以往研究也多将之划分为“雁门关以北”为河东石敬瑭所控的云、应、朔、寰、蔚五州,以及“卢龙一道”为幽州赵德钧所制的幽、涿、蓟、檀、顺、瀛、莫、新、妫、儒、武十一州。这样的划分一方面是受史书记载模糊所影响,如《旧五代史》称之为“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3],《资治通鉴》载为“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4]等,一方面是缺乏对五代尤其是后唐政区地理沿革史料的充分梳理与认知,也未充分利用历史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故而多以河东、幽州两大部分对十六州之地进行区分讨论。然而,唐末五代时期的政治地理时有变更,十六州之地既不能笼统的归为河东所属、幽州所制,亦不能因石敬瑭身居“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5]之职而认为其对雁门诸州的控制权。故而,对于十六州节制权的讨论,不是基于哪一节度使的兼领与影响,而是要讨论诸州的实际控制权以及各州节度使的政治倾向。通过对五代特别是后唐地理沿革相关史料的爬梳以及对今人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鉴,[6]以下将燕云十六州划分为三大部分进行探讨:一是幽州节度使所领幽、涿、蓟、檀、顺、瀛、莫七州,二是威塞军节度使所领新、妫、儒、武四州,三是雁门关以北的云、应、朔、寰、蔚五州。
一、幽州卢龙节度使辖下的幽、蓟、瀛、莫、檀、顺、涿七州之地
自安史之乱以来,幽州便成为长期不奉朝廷之命而割据一方的河北三镇之一,从公元763年安史降将节镇河北到公元913年晋王李存勗灭燕,幽州割据长达150年之久,幽燕之地“东有鱼盐之饶,北有塞马之利”,[7]人口相对稠密,物力较为富饶,地势更为险要,其长期割据自立的发展状况,使中央始终无法对其实现有效控制。后梁乾化三年(913)十一月,晋王李存勗率军攻灭刘守光建立的大燕国,标志着刘仁恭父子割据幽州十九年的历史宣告结束,幽州自此归属河东辖制,是年十二月李存勗即“以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此后幽州节度使久任少易,李存勗亦曾兼领。在河东李晋任命下的诸任幽州节度使中,赵德钧统辖幽州最长(925——936),达十一年之久(详见表1)。幽州归属契丹后,辽太宗及述律太后皆不喜赵德钧为人,困之不用,但赵氏在幽州历十余年经营,根基深厚,一时难以控御,为避免引发新入汉地可能引发的系列叛乱,耶律德光仍以德钧养子赵延寿为幽州节度使,以此来稳定新入汉地的内部秩序。可见,幽州并不是易于掌控更易之地,即使强如契丹也不能不有所顾虑。
表1 五代历任幽州节度使简表
时间 | 节度使 | 任期 | 备注 |
907年-913年 | 刘守光 | 6年 | 从896年至907年,刘仁恭为幽州节度使。911年八月刘守光自称大燕皇帝,913年被晋王李存勗攻灭。 |
913年12月——919年1月 | 周德威 | 5年 | |
919年1月——919年3月 | 李嗣昭 | 2月 | 周德威战死,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权知幽州军府事。 |
919年3月——923年3月 | 李存勗 | 4年 | 李存勗兼领幽州,以近臣李绍宏提举府事,故实际管辖者是李绍宏。 |
923年3月——924年3月 | 李存审 | 1年 | |
924年3月——925年1月 | 李存贤 | 10月 | |
925年——936年 | 李绍斌 (赵德钧) | 11年 | 李存贤卒,以沧州节度使李绍斌为幽州节度使。926年5月唐庄宗复其姓名为赵德钧,李绍斌即赵德钧。 |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时期,幽州向背对中原权力之争而言,往往有着重要的影响,王夫之曾言及五代“汴、晋雌雄之势,决于河北”,[8]河北最为重者则为幽州,河东晋军也正是在灭燕以解除南北两线作战的后顾之忧后,直指黄河、灭梁建唐。故而,对五代中原内部诸方势力而言,像幽州这样的割据重镇,若能为己所用,自是如虎添翼;若是为敌所控,必将后患无穷。当中原政权稳定之际,幽州自是如同其他方镇般平稳割据而已,但在五代政局极其动荡、各派势力又蠢蠢欲动的形势下,经济发达、地势险要的幽州自是各方既拉拢争取又相互攻伐的政治对象,成为中原土地上一股举足轻重而又难以把控的割据势力。赵德钧自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以来便镇守幽州,长达十一年之久,历经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四朝更迭而屹立不倒,与唐明宗李嗣源又为儿女亲家,在后唐内部威望并存,在幽州根基深厚,面对契丹南寇又能有效抵御、屡屡挫之,实为割据势力中最为强势的一方。
石敬瑭叛立爆发后,节镇幽州、实力雄厚的赵德钧亦是心怀异志:“初,赵德钧阴蓄异志,欲因乱取中原,自请救晋安寨;唐主命自飞狐踵契丹后,钞其部落,德钧请将银鞍契丹直三千骑,由土门路西入,帝许之。赵州刺史、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刘在明先将兵戍易州,德钧过易州,命在明以其众自随。在明,幽州人也。德钧至镇州,以董温琪领招讨副使,邀与偕行,又表称兵少,须合泽潞兵;乃自吴儿谷趣潞州,癸酉,至乱柳。时范延光受诏将部兵二万屯辽州,德钧又请与魏博军合;延光知德钧合诸军,志趣难测,表称魏博兵已入贼境,无容南行数百里与德钧合,乃止。”[9]其后德钧养子赵延寿“遇赵德钧于西汤,悉以兵属德钧。唐主遣吕琦赐钧敕告,且犒军。德钧志在并范延光军,逗留不进,诏书屡趣之,德钧乃引兵北屯团柏谷口”。[10]欲合诸州之兵、“志趣难测”的赵德钧,在石敬瑭叛乱爆发后,汲汲于合并诸军以扩充实力,并不想与契丹战场交锋,虽然赵德钧在唐末帝的屡屡催促下,方才引兵屯驻团柏谷,但当时张敬达被契丹大军围困于晋安寨形势早已岌岌可危,赵德钧却“欲倚契丹取中国,至团柏逾月,按兵不战,去晋安才百里,声问不能相通。”在竭力保存实力的同时,又“累表为延寿求成德节度使”,引起李从珂强烈不满:“赵氏父子坚欲得镇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虽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毙耳。”[11]显然,赵德钧一方面保持按兵不动,尽力保存自身实力,伺机而动,另一方面又不断汇合诸处兵力、屡为赵延寿求成德节度使,以扩大自己在河北的统治地盘。在这种状况之下,手握重兵、实力雄厚的赵德钧俨然已成为继后唐李从珂、河东石敬瑭两方势力之外的另一对峙力量,无论其从“欲倚契丹取中国”的政治谋划,还是作为后唐进讨河东的一方大军,赵德钧皆是石敬瑭既无法拉拢控制又无法彻底击败的强大对手。双方矛盾的迅速激化缘起于赵德钧厚以金帛贿赂契丹、截断耶律德光南下援晋一事。
晋阳起兵后,面对后唐张敬达的长期围攻,太原城困粮乏、形势蹙危,石敬瑭在中原内部仅争取到安重荣、安元信和安审信、张万迪三股约两千余骑小范围势力的投奔支持,且皆是率兵奔入太原城内,并没有在太原以外其他州县形成有效应援,石氏起兵之初预构的“外告邻方”策略收效甚微,此时唯有求诸于“北构强敌”策略的成功,契丹成为石敬瑭谋帝中原、实现不轨之志的唯一希望。在石氏生死存亡全然取决于契丹之际,赵德钧却横插一杠,打乱了石敬瑭起兵之初的政治谋划。辽天显十一年(936)七月,“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其主所讨,遣赵莹因西南路招讨卢不姑求救……时赵德钧亦遣使至,河东复遣桑维翰来告急,遂许兴师。”[12]石敬瑭自五月起兵已先后两次派使求援,桑维翰的二次出使与赵德钧有着极大关系,《旧五代史》卷八十九《桑维翰传》有载:“高祖领河阳,辟为掌书记,历数镇皆从,及建义太原,首预其谋。复遣为书求援于契丹,果应之。俄以赵德钧发使聘契丹,高祖惧其改谋,命维翰诣幕帐,述其始终利害之义,其约乃定。”[13]石敬瑭深惧德光改谋其实不难想象,在赵德钧发使契丹之前,石敬瑭应是同此前张文礼、王郁、王都等人求援契丹的惯例一般,即以重金厚赂契丹出兵援助,最多加上君臣父子之国的约定;赵德钧此时发使聘契丹,显然给出了远胜于石氏的利益筹码,从《资治通鉴》中所载赵德钧“厚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14]的内容亦可知一二,石敬瑭与唐末帝正处于战事焦灼之际,手握重兵的赵德钧完全有实力“即以见兵平洛阳”,耶律德光甚至可以不折损一兵一卒而尽获其金帛厚赂。一个是被重兵围困、前途未卜的末路穷主,一个是手握重兵、实力雄厚的割据雄主,如此高下立见的政治选择放在德光面前,也不免让其动摇,也足以让底气不足的石敬瑭深而惧之。故而才有了桑维翰所言的“利害之义”,即利诱契丹南下援晋的决定性筹码——“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15]
在幽州、河东两方势力皆可增加金帛以竞价的方式赢取契丹支持的情况下,石敬瑭所面临的外围形势较之赵德钧的游刃有余显然不占任何优势,并不具备与赵德钧打持久竞价战的实力和资本,张敬达大军的持续攻城也迫使石敬瑭必须速下决断,这时唯有兵行险着、出其不意,给出耶律德光无法拒绝、赵德钧又无法匹敌的邀约筹码,方能挽救目前内外交困的险恶处境,为自己赢取一线生机。在伦理道义、金银财宝丧失竞争力的情况下,割让土地成为石敬瑭思虑范围之内唯一能胜过赵德钧的最终选择:若契丹履行初约助其攻唐称帝,在原有给予金帛重赂、约为父子之国的盟好内容之外,另行割让幽云十六州之地与之。石敬瑭势要将其目前及未来的另一最大敌手赵德钧及其势力连根拔起,割让幽州及其节制下的蓟、瀛、莫、檀、顺、涿共七州之地予辽,给予赵德钧以致命痛击,使其瞬间丧失与石氏竞争的政治资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或继续作为后唐进攻石晋的军队之一,全力听从李从珂调遣,站在石敬瑭与契丹的对立面,战场交锋、兵刃相见;或是主动归降契丹,因已丧失与契丹继续盟约的政治筹码。在石、赵二人的政治较量下,早已无路可退、唯有孤注一掷地石敬瑭胜出,割地之议成功坚定了耶律德光的援晋之念,最终在契丹铁骑的增援下迅速扭转战局、建国称帝,实现了积蓄已久的称帝夙愿。相比之下,赵德钧在结好契丹失败后,先是与契丹兵刃相见、败北后又投降契丹,因不为契丹主及述律太后所喜,落得个郁郁而终的悲惨结局。由此观之,割让赵德钧控制下的幽蓟七州予辽,从五代中原内部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是石敬瑭为排除异己敌对势力、实现不轨之志而作出的政治取舍。
石敬瑭在割让幽州予辽的政治考量中,除出于中原权力斗争之需外,也应是考虑到了契丹对幽蓟汉地的长期窥伺与汲汲渴求。契丹对幽州的侵占企图自耶律阿保机时代便已显现,从907年阿保机即汗位到936年辽太宗取得幽蓟汉地,二十余年来契丹两代君主不断南下侵扰,竭力插手中原权力之争,以期打开南下中原之门户,幽州自始至终都是其南侵的第一目标所在。石敬瑭在生死存亡之际,准确地把握了契丹的扩张野心,充分地满足了其南进幽州的战略欲望,在契丹援与不援的关键时刻,石敬瑭果断选择将幽州连同其节度下的七州之地一同让与契丹,作为契丹南下援晋的部分回馈,这样的诱惑对耶律德光而言,足以使其全力援晋、出兵一试:若败,仅是如此前南下中原受挫般的一次军事失利而已;若胜,则能得幽蓟险地,打开南进中原之门户,完成其父耶律阿保机未竟之大业。故而,当桑维翰将称臣割地条约献于契丹后,耶律德光大喜过望,言于其母述律太后:“儿比梦石郎遣使来,今果然,此天意也。”“乃为复书,许俟仲秋倾国赴援。”[16]在割地幽州的重赂下石敬瑭终于换来了契丹的如期赴援,所以即使在刘知远“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的强谏下,仍不改割地条约,即是要确保契丹受幽州之利诱而出兵南下,以求得自身之生存、免遭后唐之攻灭。因此,石敬瑭之所以选择向契丹割让赵德钧控制下的幽蓟七州,乃是基于自身所面临的形势与困境,在多方考量之下作出的政治选择,既是在中原内部激烈的权力角逐下为排除异己敌对势力而做出的政治权衡,也是邀约契丹、全力确保契丹如约应援的关键筹码。
二、新州威塞军节度使所领新、妫、儒、武四州
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四州在五代初尚属幽州卢龙节度使所领,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七月,“升新州为威塞军节度使,以妫、儒、武等州为属郡。”[17]八月,“以隰州刺史张廷裕为新州威塞军节度留后。”[18]天成元年(926)六月,新州留后张廷裕“正授本军节度使”,[19]长兴元年(930)四月,唐明宗诏“改新州管内武州为毅州”。[20]唐末帝时期(934——936在位),先后任命杨汉宾与翟璋为新州节度使。赵德钧任幽州卢龙节度使是在同光三年(925)正月,新州自同光二年(924)七月已从幽州分离出去,双方不存在交集,新州亦不受赵德钧影响,在石敬瑭叛唐自立后,史籍中也不曾记载新州威塞军的相关行动与政治态度,在此期间新州威塞军应是仍奉后唐诏令、归李从珂调遣:从清泰二年(935)六月后唐末帝诏“以新州节度使杨汉宾为同州节度使,以前晋州节度使翟璋为新州节度使”,[21]直至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二月,“契丹主过新州,命威塞节度使翟璋敛犒钱十万……己亥,璋表乞徵诣阙。既而契丹遣璋将兵讨叛奚、攻云州,有功,留不遣璋,璋郁郁而卒。”[22]新州在政治表现或实际行动中皆未如幽州赵德钧般对石敬瑭的起兵造成显著威胁,但石敬瑭仍选择将之作为割地条件中的一部分奉送契丹,可能更多的是从威塞军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竭力讨好契丹的政治初衷来考虑的。
新州及其属郡妫、儒、武诸州,位于河东代北诸州的东面、幽州西面,北部与辽朝边境直接接壤,是契丹铁骑南下频繁侵扰三大地区(幽州、新州、云应诸州)之一,除儒州史料记录不甚明晰外,契丹在南侵过程中明确记载的有两次占有过新、妫、武诸州,并一度将妫州改名为可汗州、武州改为归化州。关于威塞军诸州入辽又复归中原之事:第一次是在辽神册二年(917)二月,新州裨将卢文进杀防御使李存矩叛逃契丹,旋引契丹军攻陷新州,《旧五代史》载:“契丹攻新州甚急,刺史安金全弃城而遁,契丹以文进部将刘殷为刺史。”[23]新州一度为契丹据有,至神册二年(917)八月,契丹在幽州城下惨败于李存审、李嗣源率领的晋军,被迫撤退,当此之际,“契丹主力既退出幽州之境,云州又属李晋。新州突入中原,难以守御,故卢文进及契丹军又弃之而去。”[24]新州首次入辽时间不满半年。其中妫、武二州入辽时间上比新州略早,神册元年(916)十一月,契丹“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25]次年(917)八月随着新州复归李晋,武、妫二州亦随之同归中原。诸州第二次入辽,实缘起于921年中原爆发的镇、定之乱,“晋新州防御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于契丹,而关于王郁仅是率众附辽还是连同新州一举归辽,余蔚先生认为王郁是举地入辽,“王郁降后,‘山后诸州皆叛’,阿保机立即‘率大军入居庸关’。居庸关门户洞开,正是新州失陷的后果。”[26]在新州叛降契丹的同时,武州、妫州亦复降。次年(922)河东李晋再度收复除新州外的武、妫等州,正月,“晋代州刺史李嗣肱将兵定妫、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团练使。”[27]儒州也在其中,可知儒州亦曾随武、妫二州短暂入辽数月。随着河东李晋军队不断攻陷入辽的山后诸州,契丹对新州的统治愈发艰难,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正月“幽州奏,妫州山后十三寨百姓却复新州”,[28]新州再次归属中原所治,此次新州入辽达两年有余。也可能基于新州在契丹与中原交战中的战略地位与攻易变化,同光二年(924)正月新州复归后唐后,李存勗着力提升新州地位,三月即“升新州为威塞军节度使,以妫、儒、武等州为郡属”,[29]使其脱离幽州卢龙节度使管辖而自为节度。
正如契丹在神册元年(916)攻陷新州数月后却又不得已而放弃那般,因辽军“主力既退出幽州之境,云州又属李晋。新州突入中原,难以守御,故卢文进及契丹军又弃之而去”,[30]石敬瑭在考虑割地范畴时亦可能有过同样的顾虑,新州之东的幽州既是不能容忍的必割之地,新州之西的云应诸州又是不得不割让之地(下文将着重论述),若贸然保留新州,势必也会因其地理突入契丹、难以守御而落得个与契丹边界摩擦不断、甚而再度舍弃的不利境地。与其如此,不如满足契丹此前两度侵驻的扩张欲望,将这个今后可能引起辽、晋双方边境冲突的敏感地带直接与之,也为契丹南下更添一份有力诱惑。久蓄异志而又处境蹙危的石敬瑭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会因数州之地利而使自己求援契丹的诚意受到一丝丝质疑,割让除河东、幽州之外的新州及其属郡妫、儒、武诸州,成为石晋竭力满足契丹侵略欲望、加大契丹赴援砝码而作出的政治选择。
三、雁门关以北云、应、寰、朔、蔚五州
后唐长兴元年(930)因“契丹自幽州移帐,言就放牧,终冬不退”,[31]云朔诸州备受其患,石敬瑭为避后唐内祸自请北行御敌,是年十一月,唐明宗授其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32]唐闵帝应顺元年(934)年二月曾一度徙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李从珂夺位后旋即于当年五月复“以成德军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都部署、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驸马都尉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都部署如故”。[33]清泰二年(935)为备御契丹南寇,石敬瑭率大军屯驻忻州,六月“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传诏抚谕,军士呼万岁者数四。敬瑭惧,幕僚河内段希尧请诛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刘知远斩挟马都将李晖等三十六人以徇”,[34]唐末帝对石敬瑭更为猜忌,寻令“徐州节度使张敬达充北面行营副总管”,“以减敬瑭之权”。[35]从长兴元年(930)年十一月到清泰三年(936)五月拒诏叛立前夕,石敬瑭在河东经营五年有余,然其实际控制与影响的地区是有限的。石敬瑭所割让雁门关以北云、应、寰、朔、蔚五州,虽然在地理上属河东地界,但并非全受石敬瑭控制与影响。石敬瑭虽身居“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36]但并不意味着对代北诸州皆有控制权。在五代藩镇拥兵自重的情况下,当内外调令一致、皆听命于中央战略部署下的北面蕃汉马步总管对诸军兵马是有一定的领导调控权的,但当其与中央诏令背道而驰甚而兵刃相见、战场交锋时,一切便取决于各州的实际控制者而非兼领之人。云、应、朔、寰、蔚诸州的实际控制权在河东起兵前后仍然掌握在后唐任命的各州节度使手中,皆非石敬瑭所控,石氏真正能掌控和影响的仅是其作为河东节度使治所的太原及其属郡。
石敬瑭所割让的雁门关以北诸州,按照实际控制权而言,分别是隶属于云州节度所领之云州,彰国军节度使领下的应、寰二州,振武军节度使治所朔州,以及归河东节度使管辖的蔚州。云州为唐末旧镇,五代以来先后经历大同军、防御州、刺史州等军额的反复变化,辖区也由最先的云、朔、应、蔚四州逐渐缩减至仅辖云州一州(详见表2)。朱玉龙先生最早对之沿革变化进行梳理:“大同军节度使、云州刺史、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唐旧镇。唐末属河东,废为防御使额。五代后梁贞明元年,复置,节度使李存璋卒,降为刺史州,仍领雁门以北都知兵马使。后唐同光二年七月,复为大同军节镇,改领云、应二州。天成元年七月,析应州别置彰国军,此后有无支郡即不详。石晋献地,割属契丹。”[37]其中,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将其原先所辖应州分离出去后,云州节度使除直接管辖云州外应再无其他支郡。[38]云州节度使(前期亦称大同节度使)的任期多不长,最长者为李存璋,有六年之久,其他多是长者两三年、短者数月而已(参见表3),较之幽州而言,这样的频繁更易导致云州不易坐大割据,有利于中央的有效控御。从长兴元年(930)石敬瑭出任“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39]到清泰三年(936)起兵叛立后,云州节度使先后经历四任——张敬达、张温、安重霸、沙彦珣,张敬达作为后唐讨伐石晋的军队主帅自是与石敬瑭在政治上相向而立,张温、安重霸和沙彦珣皆任职于唐末帝时期,但张温在清泰二年(935)正月移镇晋州后,不久即“婴疾而卒”,[40]安重霸同样于是年八年卒亡,最后一任云州节度使即是沙彦珣。沙彦珣在后唐覆灭前,始终听命于唐末帝调遣,后唐清泰二年(935)年六月唐末帝以“前彰国军节度使沙彦珣为右神武统军”,[41]七月“以右神武统军沙彦珣权知云州”,[42]八月“以权知云州、右神武统军沙彦珣为云州节度使”。[43]清泰三年(936)年七月云州发生桑迁谋应河东的叛乱,“云州节度使沙彦珣奏,此月二日夜,步军指挥使桑迁作乱,以兵围子城,彦珣突围出城,就西山据雷公口。三日,招集兵士入城诛乱军,军城如故。”[44]沙彦珣果断镇压桑迁之乱,云州仍掌握在沙彦珣手中,此时沙彦珣的政治态度依然是拥护后唐末帝的统治;八月,“己巳,云州沙彦珣奏,供奉官李让勋送夏衣到州,纵酒凌轹军都行,劫杀兵马都监张思殷、都指挥使党行进,其李让勋已处斩讫。”[45]后唐朝廷使者与指令皆能通达于云州,沙彦珣亦能奏表唐末帝,表明后唐仍能有效掌控云州,这样的控制直到后晋天福二年(937)二月,契丹回师过云州,沙彦珣不得已出城迎接,契丹主遂留之不遣,沙彦珣归降契丹,但云州亦未遵从石敬瑭的割让条约顺利入归契丹,反而在吴峦的主持下率众据城反抗达数月之久后方才被迫入辽。由此可见,云州自始至终处于石敬瑭的政治对立面,不受石氏控制和影响。
表2 五代初云州辖区沿革表
时间 | 军额升降 | 辖地 | 备注 |
908年1月 | 大同军节度使 | 云州、朔州、 应州、蔚州 | 天祐五年正月升云州为大同军节度使 |
908年2月 | 云州防御使 | 云州、朔州、 应州、蔚州 | 2月,大同节度使李克宁伏诛,降云州为防御使。 915年6月曾一度授贺德伦为大同军节度,后因贺德伦被斩不曾到任,故而云州在916年之前仍旧为防御使额。 |
916年6月 | 大同军节度使 | 云州、应州、蔚州 | 916年因李存璋退敌有功,由大同防御使、应蔚朔等州都知兵马使升为检校太傅、大同军节度使、应蔚等州观察使。 |
922年4月 | 云州刺史 | 922年4月李存璋卒,云州降为刺史州。 | |
924年7月 | 大同军节度使 | 云州、应州 | 924年8月以云州刺史、雁门以北都知兵马使安元信为大同军节度留后。 |
926年 | 云州节度使 | 云州 | 应州于天成元年7月升为彰国军节度使。至936年石晋献地,云州归属契丹。 |
表3 五代初云州节度使沿革表
时间 | 节度使 | 备注 |
908年1月-2月 | 李克宁 | 正月升云州为大同军节度使,李克宁为节度使。2月大同节度使李克宁伏诛,降云州为防御使。李克宁之后史料未载何人接任大同节度使。 |
915年6月-916年2月 | 贺德伦 (未到任) | |
916年——922年4月 | 李存璋 | 李存璋卒于任上 |
924年8月——925年2月 | 安元信 (留后) | 安元信为大同军节度留后,后调任沧州节度使。 |
925年2月——12月 | 李存敬 | 《旧五代史·庄宗纪六》载“十二月壬戌,以前云州节度使李存敬为同州节度使”,李存敬很可能是在安元信调任沧州后出任云州。[46] |
925年12月——927年4月 | 高行珪 | 926年六月丙申,云州留后高行珪正授本军节度使。 |
927年4月——928年9月 | 张敬询 | 927年4月,以利州节度使张敬询为云州节度使。9月,以前云州节度使高行珪为邓州节度使。 |
928年9月——928年10月 | 索自通 | 928年9月,以捧圣左右厢副都指挥使索自通为云州节度使。 |
928年10月——929年6月 | 张敬询[47] | |
929年6月——930年3月 | 杨汉章 | 926年6月,夔州节度使杨汉章移镇云州,10月以云州节度使张敬询为左骁卫上将军。 930年3月,以前云州节度使杨汉章为安州节度使。 |
930年11月——933年3月 | 张敬达 | 930年11月应州节度使张敬达移镇云州。 |
933年3月——935年1月 | 张温 | 933年3月以右龙武统军张温为云州节度使,10月以前云州节度使张敬达为徐州节度使。 |
935年1月——8月 | 安重霸 | 935年正月以张温移镇晋州,以西京留守安重霸为云州节度使。 |
935年8月——937年2月 | 沙彦珣 | 935年8月以权知云州、右神武统军沙彦珣为云州节度使。936年石晋割地献辽,937年2月契丹主过云州,留之不使还镇。 |
应州原属大同军节度,后唐明宗时升之为彰国军,以寰州属之。后唐天成元年(926)七月,唐明宗“升应州为彰国军节度,仍以兴唐军为寰州,隶彰国军。”[48]“应州,故属大同军节度,唐明宗即位,以其应州人也,乃置彰国军。”[49]应州彰国军节度使共历五任:李从璋(任期:927年8月——928年2月)、孙汉韶(任期:928年3月——929年6月,节度留后)、张敬达(任期:929年6月——930年11月)、沙彦珣(任期:930年11月——934年6月)、尹晖(任期:934年12月——936年石晋割地)。以上已论及张敬达、沙彦珣的亲唐态度,最后一任节度使尹晖与唐末帝更是渊源颇深。后唐应顺元年(934)年三月,闵帝派王思同率同讨伐潞王李从珂,“凤翔城堑卑浅,守备俱乏,众心危急,”在此危难之际,唐将杨思权“帅诸军解甲投兵,请降于潞王,自西门入”,[50]王思同“犹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晖大呼曰:‘城西军已入城受赏矣。’众争弃甲投兵而降,其声震地。日中,乱兵悉入,外军亦溃,思同等六节度使皆遁”,[51]凤翔战局也由此发生逆转,李从珂率众一路东下,攻破洛阳,成功夺取帝位。作为首归之人的尹晖,李从珂曾“约以鄴都授之”,其后也颇受器重。然尹晖与石敬瑭的关系却并不融洽,两人在末帝朝初即互相结怨:“末帝即位,高祖(按:石敬瑭)入洛,尝遇晖(按:尹晖)于通衢,晖马上横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后因谒谓末帝曰:‘尹晖常才,以归命称先,陛下欲令出镇名籓,外论皆云不当。’末帝乃授晖应州节度使。”[52]本可授名藩的尹晖在石敬瑭的阻隔下于清泰元年(934)十二月出镇应州,是为彰国军节度使。石敬瑭叛立爆发后,是年(936)七月发生了云州桑迁叛乱:“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奏应州节度使尹晖逐云州节度使沙彦珣,收其兵应河东。丁酉,彦珣表迁谋叛应河东,引兵围子城。彦珣犯围走出西山,据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击乱兵,迁败走,军城复安。是日,尹晖执迁送洛阳,斩之。”[53]尹晖将桑迁送归洛阳处置,自是在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加之其与石敬瑭之间的旧怨,尹晖不会在石氏受困、形势窘迫的情形下而与之结好。即使石敬瑭称帝建晋后,两人的关系也并未缓和:“时范延光据鄴谋叛,以晖失意,密使人赍蜡弹,以荣利啖之。晖得延光文字,惧而思窜,欲沿汴水奔于淮南。高祖闻之,寻降诏招唤,未出王畿,为人所杀。”[54]尹晖在后晋政治失意、处处谨慎防备与此前其作为后唐应州节度使与石敬瑭政治对立、互有嫌怨有很大关系。故而,在石敬瑭叛立期间,尹晖节镇下的应州及其支郡寰州仍属后唐末帝调遣,非受石敬瑭控制和影响。
朔州,五代初隶属云州大同节度使所领,晋天祐十九年(919)年振武军节度徙治所于朔州,朔州从大同节度使领下脱离出来,与麟州、胜州共归振武军节度使管辖。从明宗朝开始,朔州振武军节度使与石敬瑭并无历史交好记载:唐明宗时先后有安金全、张温(留后)、张万进、高行周、杨光远出任振武军节度使;闵帝即位后,于应顺元年(934)正月“以振武军节度使、安北都护杨檀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都虞候,充北面马军都指挥使。”[55]李从珂夺位称帝后,于清泰元年(934)十一月“以振武节度使杨光远充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兵马都虞候”,[56]十二月“以北面马军都指挥使、易州刺史安叔千为安北都护、振武节度使”。[57]在石敬瑭叛乱爆发前后,朔州与石敬瑭并不存在实质性隶属关系或节度使间的个人私交。清泰三年(936)五月河东叛立后,朔州依然听命于唐末帝号令,时“振武节度使安叔千奏,西北界巡检使安重荣驱掠戍兵五百骑叛入太原。”[58]八月,末帝又“以振武军节度使安叔千充代北兵马都部署”。[59]虽然清泰初安叔千曾有着“从晋祖迎战”契丹于雁门的战事经历,在后唐覆灭后也继续仕任于石晋朝,但在石敬瑭与李从珂政治对立期间,朔州并没有有过任何的军事应援或政治倾斜,依然如实向后唐朝廷奏报前线状况,作为振武军节度使的安叔千仍奉后唐诏令,朔州亦不受石敬瑭制衡与影响。
综上而论,云州节度使沙彦珣、应州彰国军节度使尹晖(领寰州)、朔州振武军节度使安叔千皆听命于后唐政权,服从于唐末帝李从珂的调遣。换言之,石敬瑭所割让的雁门关以北五州中,云、应、朔、寰四州皆属后唐李从珂势力掌控,既不归河东节度使所辖,也不受石敬瑭控制和影响,与之反处于政治对立面。割让契丹的代北诸州中,仅蔚州一地属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所领。早在唐末五代初,河东节度使确实辖有太原府及仪、石、岚、汾、代、忻、朔、蔚、云、应、宪、慈、隰诸州,其后云州升为大同军节度,以朔、应、蔚州属之,从河东节度使领下独立出来,虽之后仍反复和沿革,但在后唐庄宗同光年间(923—925),河东节度使所领太原府及辽、石、岚、汾、代、忻、宪、府、蔚诸州的辖区范围基本延续至石晋割地前,[60]石敬瑭出任河东节度使是在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十一月,其所领地理格局承袭自明宗朝,在清泰三年(936)选择割让雁门诸州之际,石敬瑭实际上仅仅出让了其管辖范围内的一州之地,即蔚州。蔚州的割让,石敬瑭也是根据形势与需求而进行选择的:首先,蔚州虽属河东节度使所领,然其与石氏势力联系并不紧密,中间又横亘着其他州地,在太原起兵自立后,蔚州并未有过任何声援和倾靠,与石氏政治利益联系并不紧密,仅是归属河东节制下的一个并不凸显的边境州县而已;其次,蔚州以北是契丹铁骑常年掳掠攻伐之所,蔚州以西的云应诸州,东面和北面的幽蓟、新武诸州,皆是必割之地,蔚州在地理上恰夹于这两方地区之间,若贸然留之则显突兀,其后在契丹东、西、北三面围攻之下,蔚州处境也会十分艰难,更易滋生边界摩擦,如同新州威塞军一般,加之为示“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61]的求援诚意,石敬瑭也不会为此一州之小利而犹豫徘徊。故而,从蔚州的政治倾向、地理位置以及示好诚意方面来言,石晋方面在割地取舍上似乎没有保留的理由。
在明确代北诸州的实际控制权及其与石氏势力之关系后,可以对石敬瑭割让云、应、朔、寰、蔚五州的政治考量试作一分析:首先,割让代北诸州是石敬瑭不得已而行之、对己利益损失最小化的政治选择。上文已论述太原城困之际,赵德钧的横插一杠打乱石氏的求援计划,危在旦夕的石敬瑭决定以割地方式加大筹码,割让幽蓟、代北诸州予辽,其中因与赵德钧的针锋相对,幽州成为石敬瑭必然出让的地区选择,但石敬瑭不可能仅以出让赵德钧的利益便可获取契丹的倾力赴援,若只是割让幽蓟诸州,对正欲趁乱“倚契丹取中国”的赵德钧而言,只会给予其效仿自己而以割让河东为筹码进行加价竞争的的可能,凭空再添变故;对于契丹而言,石敬瑭若全然保存河东地界而不作任何割舍,仅靠慷他人之慨而得利己之益,似乎也不大可能,邀约契丹的诚意也会大打折扣。石敬瑭只能是在割舍自己部分利益的前提下出让赵德钧的利益,方能既不给赵德钧继续竞争的机会,也使契丹感受到其求援诚意。此外,云朔地区亦是其契丹南侵的重点地区,特别是耶律德光在援助王都失败后,契丹的侵略重点逐步从幽州转移到代北一带,常年侵扰云朔地区,而石敬塘除割让幽蓟之外,又将近年来契丹频频南侵、尚未达成之目标拱手与之,完全契合了契丹南下中原的既定经略,充分满足了契丹以前屡次南下插手中原事务的政治目的。故而,河东之地是必然要有所割舍的,石敬瑭选择割让听命于后唐末帝号令、与其站在政治对立面的云、应、朔、寰四州,以及虽受河东所辖但并无利害关系的蔚州,这样虚实结合的地理选择,极易给人造成石氏出让了自己在河东部分利益的假象。然细细究之,即使是割让代北诸州也是利用后唐李从珂的利益与契丹作交换,石敬瑭在河东地区出让的也只是与其无关利害关系的蔚州一地而已,基本上没有损失其既有(称帝前)的政治利益。
其次,在割让云、应、朔、寰、蔚五州之际,石敬瑭选择将中原政权与契丹的北部边界线(河东接壤部分)划定在雁门关以北一带,保留了代州、忻州及雁门关等地,以此保障太原北部之安全,确保河东之门户有险可守。如胡三省所言:“人皆以石晋割十六州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余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汉建安丧乱,弃陉北至地,不害魏、晋之强也。”[62]其所言“犹有关隘可守”即是指雁门关,雁门关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顾祖禹亦曾言雁门之冲的代州“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63]虽然石敬瑭不得已割让了代北五州,但割让之州皆位于雁门关以北,保留了代州、忻州等太原北部的门户重镇,特别是被誉为“天下九塞,雁门为首”的雁门关,既使得太原外围保留有足够的战略缓冲地带,也使得石晋可依恃雁门关依山傍险、东西山峦层叠起伏的天然地势以有效应对此后可能面临的契丹南下,雁门关地区也确成为其后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激烈交锋的战地之一。太原对于石敬瑭而言是至为重要的,不仅是河东地区的政治核心所在,也是后唐最初起家的源地所在,更是政权中心洛阳的北部门户,当然也是石敬瑭的出身之地,当雁门天险能够有效阻挡外敌南下,保障太原战略安全的同时,便是保障了政治中心洛阳的安全。故而,即使是出让代北诸州,石敬瑭也是在充分保障自身外围安全、尽力不损伤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作出的政治取舍。
结 语
割让幽云十六州,是石敬瑭为获取契丹援助给出的关键性筹码,辽太宗也因地利之诱而弃赵德钧之结好,亲率五万铁骑倾力赴援,一战而败后唐大军,册立石氏为帝。石敬瑭如愿实现其不轨之志、称帝中原,契丹也因之一跃而成为凌驾于中原王朝之上的异族上国,颠覆传统华夷藩属秩序,开启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与南方中原王朝鼎峙而立的又一南北朝时期。在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中,其主人公石敬瑭所做出的任何举动皆不是仓促盲然之举,而是深思熟虑、多方权衡下作出的对己利益最大化选择。在分属于幽州节度使所领幽、涿、蓟、檀、顺、瀛、莫七州,威塞军节度使所辖新、妫、儒、武四州以及雁门关以北的云、应、朔、寰、蔚五州的三方汉地之中,幽州赵德钧显然是与其针锋相对的另一敌对势力,除蔚州以外的代北四州皆是石敬瑭为求援契丹而所不得不做出的割舍之地,新州则恰处于这两方势力之间又曾多次被契丹占有,为应对中原激烈的权力斗争、排除异己敌对势力,也为充分表达其“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的求盟诚意,更为加大邀约砝码坚定耶律德光的援晋之心,石敬瑭最终选择以割让十六州为邀约契丹的关键筹码。然而即使是出让土地,石敬瑭也是利用赵德钧和李从珂的既有政治利益与契丹作交换,真正属于河东辖制、与石氏利益相关的仅仅是蔚州一地而已,石敬瑭的政治算盘打得甚是响亮,精明地做到了虚实结合下的慷他人之慨而得利己之益。总而括之,无论是割地予辽,还是父事契丹,石敬瑭皆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在多方考量之下做出的利益权衡与政治取舍。
[1]本文系“内涵发展——研究生教育立项及学位点建设及学生立项”(编号:002185507200)《石敬瑭割让燕云历史背景的再探讨》课题的研究成果。
[2]目前学界关于石晋何以割让十六州这一议题进行讨论主要是罗亮先生,其文《以谁为父:后晋与契丹关系新解》(《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对此有过简要论述,主要观点是:“石敬瑭提出的割地计划,不过是将自己部分掌控的贫瘠、在雁门关防线之外的云、朔等五州与和自己丝毫无涉、被赵德钧完全掌控的富饶且在平营防线之下的幽、蓟等十一州捆绑割让给契丹。自己出让的利益较少,而损害赵德钧的利益极多,这样就使得赵德钧难以给出同样的筹码,从而确保自己能获得契丹的援军。”
[3]《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89页。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46页。
[5]《旧五代史》卷43《唐明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96页。
[6]本文关于五代地理沿革的论述重点参考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孙钰红《五代政区地理研究——燕晋地区部分》(复旦大学年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李晓杰《五代时期幽州卢龙节度使辖区沿革考述》(《历史地理》第25辑)等今人论作。
[7]《旧五代史》卷135《刘守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04页。
[8](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8《五代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74页。
[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52—9153页。
[1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53页。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55页。
[12]《辽史》卷3《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页。
[13]《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162页。
[1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55页。此条史料虽载于天福三年(936)十一月,然亦可一窥赵德钧此前之态度,罗亮在《以谁为父:后晋与契丹关系新解》(《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中已有讨论:“此事《通鉴》虽将其系于天福元年闰十一月,但赵德钧与契丹的接触是经常性的,求立为帝、结为兄弟之国的意愿亦早已表达。”并认为石敬瑭的割地条约是在听闻赵德钧结好契丹一事后而派桑维翰重新增加的砝码,发生在该年七月。
[1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46页。罗亮《以谁为父:后晋与契丹关系新解》(《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中已经指出“利害之义”所指。
[1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47页。
[17]《旧五代史》卷32《唐庄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8—439页。
[18]《旧五代史》卷32《唐庄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9页。
[19]《旧五代史》卷36《唐明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99页。
[20]《旧五代史》卷41《唐明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65页。
[21]《旧五代史》卷47《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48页。
[2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1《后晋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70页。
[23]《旧五代史》卷28《唐庄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89页。
[24]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第5章《西京道府州县沿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4页。
[25]《辽史》卷1《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页。关于妫、武二州是否在神册元年被耶律阿保机改名一事,学界有不同看法,笔者认同余蔚先生的看法,改名之事在神册元年曾发生过。(详见《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7-248页)
[26]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第5章《西京道府州县沿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5页。
[2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1《后梁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873页。
[28]《旧五代史》卷31《唐庄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27页。
[29]《旧五代史》卷32《唐庄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8—439页。
[30]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第5章《西京道府州县沿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4页。
[31]《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8页。
[32]《旧五代史》卷43《唐明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96页。
[33]《旧五代史》卷46《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34—635页。
[3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9《后唐纪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31页。
[35]《旧五代史》卷47《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50页。
[36]《旧五代史》卷43《唐明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96页。
[37]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24页。
[38]孙钰红认为此后云州再无支郡:“自应州升为彰国军节度后,《旧五代史》中未有‘大同军节度使’之称,都以‘云州节度使’代之,如《旧五代史》卷38《明宗纪四》载:‘以前利州节度使张敬询为云州节度使。’卷39《明宗纪五》:‘以捧圣左右厢副都指挥使索自通为云州节度使。’等等。且史书中并未载有云州大同军节度使增领其他支郡,笔者认为此大同军节度使仅辖云州一州,大同军节度使随之改称为云州节度使。”(孙钰红:《五代政区地理研究——燕晋地区部分》,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1页。)
[39]《旧五代史》卷43《唐明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96页。
[40]《旧五代史》卷59《张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99页。
[41]《旧五代史》卷47《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49页。
[42]《旧五代史》卷47《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50页。
[43]《旧五代史》卷47《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52页。
[44]《旧五代史》卷48《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63页。
[45]《旧五代史》卷48《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64页。
[46]此处将李存敬作为云州节度使的划分,依据朱玉龙先生《五代十国方镇年表》的记载。(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26页)
[47]《旧五代史》卷39《唐明宗纪》载:天成三年(928)十月“以前云州节度使张温复为云州节度使”,(《旧五代史》卷39《唐明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43页)朱玉龙先生认为此处“张温”应为张敬询之误,张温节制云州应是在长兴末、清泰初,其他史书也皆无张温天成年间领镇云州的记载,故而疑“张温”为“张敬询”之误。(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28页)
[48]《旧五代史》卷36《唐明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02页。
[49]《新五代史》卷60 《职方考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9页。
[5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9《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07页。
[5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9《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08页。
[52]《旧五代史》卷88《尹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154页。
[5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46页。
[54]《旧五代史》卷88《尹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154页。
[55]《旧五代史》卷45《唐闵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16页。
[56]《旧五代史》卷46《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40页。
[57]《旧五代史》卷46《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40—641页。
[58]《旧五代史》卷48《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61页。
[59]《旧五代史》卷48《唐末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64页。
[60]此部分关于河东节度使辖区沿革的论述皆参考孙钰红硕士论文《五代政区地理研究——燕晋地区部分》(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4-37页)。
[6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56页。
[6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154页。
[6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0《山西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49页。
【编辑】鲁畅
宋史研究资讯
欢迎订阅『宋史研究资讯』
微信号:songshiyanjiu
信箱:
- 热门文章
- 最近发表
- 标签列表
-
- 最新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