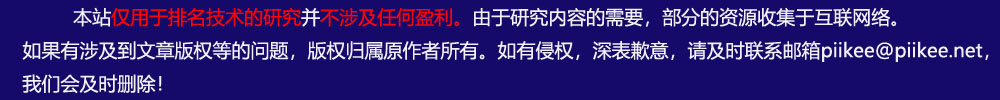野花社区看日本迷片(野花论坛最)
2008年5月12日那场地震里,北川中学初三四班37人全部幸存。
十年后,这群昔日十五六岁、穿着校服的少男少女已经长大,生活的重心也从学习变成了工作、结婚、生子。
班上的女生陆春桥把镜头对准他们中的三个人,拍摄了一段32分钟的纪录片,取名为《初三四班》。
“太多的片子在讲地震后的悲伤痛苦,却没有人去讲我们对生活的珍惜”,陆春桥提起拍摄的初衷,是希望记录下他们这代人的成长,讲讲他们是如何在经历灾难后,去理解家庭与爱的。
2008年9月,地震后初三四班第一次合影。受访者供图
揭开伤疤
12月26日,陆春桥拍摄的纪录片将在腾讯视频上线。纪录片的开始,是一场同学聚会。
2016年大年初三,陆春桥组织了一场初三四班同学会。那天,她扎着高高的丸子头,带着摄像机回到北川中学。
在陆春桥的镜头中:阳光铺满整间教室,蓝色桌椅整齐地摆放着。八年未见的同学按初中毕业时的座位坐下。
大家显得有些生疏。有人提议,轮流站上讲台,重新做自我介绍,分享这些年的经历。
女生母志雪穿了身亮眼的红大衣,化了淡妆,她站上讲台,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几年过得特别好”,同学们在底下都笑开了。
在陆春桥的记忆中,母志雪是个内向的人。初中时,她坐在陆春桥后面的座位,扎马尾辫,穿最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非常文静,不爱说话。
但现在,她跟每个人都热络地开玩笑。她说她现在在施工队工作,梦想是当个包工头。
2016年大年初三,母志雪在同学会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男生何林烛也站上了讲台做自我介绍,镜头中他平头,浓眉大眼。和初中时相比,变化不大,依旧外向、善于交际。
他高三辍学,留在北川,送过外卖、当过KTV服务员、开过婚庆用品店,是同学们心中的励志担当。
聚会那天,陆春桥拍了不少视频和照片。回去翻看时,她发现,同学们虽然都很年轻,但是看上去要比同龄人更成熟一些。陆春桥很好奇,“那场大地震到底是如何改变了我们这群人的生活?”
多年来,陆春桥和同学们很有默契,鲜少谈论与地震有关的话题。上大学去了外地,他们也不会主动跟同学提起自己来自北川。
陆春桥想,他们这些年的故事值得记录下来。地震过去8年,关于北川的故事,别人已经讲得够多了,如果换作自己来讲,会不会不一样?
要重新揭开这块伤疤,并不容易。幸好是陆春桥来做这件事。初三四班的刘文静说,“别的记者来采访,总会有被消费的感觉,但她不一样”。她相信,陆春桥和他们是同类,对那段过往能产生共情。
幸存者陆春桥
陆春桥曾是班上最爱好文艺的女孩。上高中后,开始跟市里来的艺术老师学编导,大学在南京学摄影,毕业后去了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工作。
2015年6月,陆春桥上大四,和制片人韩轶聊天时,说起了那场地震。韩轶提议,这帮孩子的成长或许能拍个纪录片。陆春桥被打动了。
她先是挨个给同学们打电话,久疏联系,陆春桥发现,原来她对老同学这么不了解:地震后,他们失去了哪个家人、经历了哪些痛苦、有没有走出来……她一无所知。于是,陆春桥回到北川,开始跟同学和他们的家长详细访谈。
在纪录片中,陆春桥访谈了自己的父亲,那天,父亲开着车,母亲躺在后座。父亲漫不经心地聊道:
“地震那天买了四吨多厚朴花,遇到地震了,就全部变成垃圾了,跟你妈在片口困了两天。房子摇过去摇过来,就像跳舞一样。第二天用柴油机发的电,看到新闻,说北川中学三楼变成一楼了。我想女儿肯定死了,你妈就哭了,她整天都在哭,最后就要来找。”
2008年5月12日地震来的时候,初三四班所有同学都在室外上体育课,陆春桥站在报栏前看报。一瞬间,世界开始摇晃,教学楼倒了,漫天的灰尘扑过来,不远处的山被滚落的巨石、泥土包裹住,由绿变黄。
幸运的是,在操场的初三四班同学们都活了下来。
地震过后,北川中学的学生都被转移到了六十公里外的绵阳长虹影剧院。每天,影剧院都会播放寻人广播,“XXX同学,你的家人在找你”。第三天晚上,陆春桥躺在纸板上准备睡觉时,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她匆匆穿上长虹发的拖鞋,赶到影剧院门口。看见母亲站在人群中,背着一个双肩包,拄着一把伞,衣服破破烂烂,脚上还穿着陆春桥留在家里的胶鞋。母亲原本白皙的皮肤也变得黝黑,一下子老了十岁。陆春桥想给她换上自己的拖鞋,才发现胶鞋已经陷进了妈妈的肉里,根本脱不下来。
陆春桥的父母接受采访。受访者供图
母亲旁边不见父亲的身影,她告诉陆春桥,父亲的哮喘犯了,只好在家等着。这个从没落过泪的男人,还偷偷钻到了厕所里哭。
那年10月,陆春桥的妈妈生了一场重病。医生说,是因为地震之后,她的精神处在崩溃边缘,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导致她患上了植物神经紊乱。心理上的表现是焦虑、抑郁,生理上则表现为胸闷、憋气等症状。
在此之前,陆春桥一直以为,电视里演的抑郁症等心理疾病都只是单纯的心情不好。妈妈得病以后,她才知道,“原来情绪也可以杀死人”。
许多同学的家庭都被这场地震拆散了。母志雪失去了父亲,地震时,他正在矿山上工作,没跑出来。何林烛失去了六岁的弟弟,那是一个活泼聪明的小男孩,头顶有两个旋。
陆春桥一家是幸存者,同学黄金城一家也一样。他告诉陆春桥,有时走在街上,会碰到一些故去同学的父母,他总会低着头,绕得远远的,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打招呼。
“生活像吃糖一样甜”
母志雪父亲在世时,希望她将来能当老师或者会计,过安稳轻松的生活。高考填志愿,她却决定去南充的一所专科学校学土木工程,“修出结实的房子、结实的路,会特别有成就感。”
在大学,同学听说她来自北川,免不了问几句地震时的情况,母志雪并不抗拒。但他们听说她父亲遇难后,总会用同情的目光打量她,这让母志雪受不了,“我会跟他们说,不要心疼我,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只是比你们多经历了一点”。
2016年,陆春桥找到母志雪时,母志雪正在成都的一个工程队工作。她负责做施工资料,记录施工的全过程,要成天跟着工程队到处跑,“和工人待在一起很开心,特别喜欢这样的生活”。
那时,她刚开始谈恋爱,没过多久就决定结婚,“随时都像吃了糖一样甜”。丈夫陈翔性格内向,陆春桥来家里拍摄时,他会害羞,藏到厕所里。母志雪笑称他是“贤内助”,和自己的性格正好互补。
结婚后,母志雪一闲下来,就会带着陈翔回老北川逛逛,给他讲自己玩过的地方、读书的地方、和父母一起去过的地方。
进入老北川,要经过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狭窄到只能容纳两辆车经过。曾经热闹的县城只剩下了断壁残垣,四处是东倒西歪的楼房。一扇扇破碎的窗户里,藏着剥落的墙面和倾倒的家具。从地缝中探出头的杂草和野花,是这里仅剩的生机。
陆春桥说,她回小坝乡时,也会经过老县城,“到现在都好像还能闻到当年石灰粉和消毒水的味道”。
地震后,母志雪的母亲以为母志雪已经不在了,带着小儿子到北川中学,打算“翻死人”。见母志雪还活着,仨人哭作一团。母志雪问,爸爸呢?母亲只是摇了摇头。
失去丈夫以后,母志雪的妈妈整天以泪洗面,也吃不下饭。为了逗母亲开心,母志雪每天给妈妈打电话,讲笑话、打趣。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她也逼着自己开朗起来,没心没肺地笑,不希望被特殊对待。
慢慢地,母志雪发现,她喜欢这个“把心放得很大”的自己。“对我来说,我已经够幸运了,至少老天还给我留下了妈妈和弟弟”,母志雪说。原本,母亲要和父亲一起去矿上上工,那天却鬼使神差地没有去。
母志雪的母亲在领了几个月的救济金后,谢绝了外界的帮助,决定要找一份工作,自己挣钱养活孩子。她听说陈家坝有个人卖卤肉很有名,她就跑到人家门口等,求他教自己做卤肉。
于是,小小的卤肉摊成了全家唯一的生计。“地震后我妈对我和我弟更好了”,母志雪说,“她想让我和我弟过上和普通家庭一样的生活,让我们活得更自信。”
在纪录片中,陆春桥采访了母志雪的母亲,母亲那天扎着马尾辫,一张圆脸,眼角堆满了皱纹。她没有哭,看似轻描淡写地聊起了逝去的丈夫。
“他们一起干活的有11个人,11个人一个都没出来。一年后,那边修路,又把他的尸体挖了出来,我又把骨头捡回来埋了。”
陆春桥问,“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其实自己的亲人就不怕,没有什么感觉”,母志雪的母亲笑了笑,“只是想着他能活过来就好了”。
何林烛的责任
在23公里之外,新北川在震后两年内拔地而起,所在地被取名为“永昌”,意为“永远昌盛”。城区整齐划一,有宽敞的马路、林立的高楼,重建了北川人的生活。
安昌河支流穿城而过,河东是现代化的居民社区、政务中心和旅游服务中心等,河西是北川中学、河西医院等公共服务建筑。在县城的中心,还修建了“巴拿恰”(羌语,意为“市场”),到过节时,羌族人民都会换上民族服饰,在这里相聚。何林烛每天就骑着电动小摩托车在新北川县城送外卖。
何林烛正在送外卖。受访者供图
2011年,高考过后,初三四班许多同学离开了新北川,到其他城市上大学。如今,许多同学都回到了新北川。
陆春桥曾问过留在新北川的同班同学:有没有后悔地震后留在北川?同学回答,去外地会被人特殊关照,但在北川不会,“这里收容了所有受伤的心灵”。
何林烛也是留下来的人。他告诉陆春桥,成都是他去过最远的地方,他原本打算在成都多待几年,因为妈妈,他决定回到新北川。
地震前不久,何林烛的父母离异了,由母亲一个人抚养他。地震后,弟弟去世,家里一贫如洗,全靠母亲在菜市场开的小店支撑。
何林烛很早就有了金钱的概念,常在中学宿舍倒卖小零食,挣个几毛钱。从家去学校距离远,走路要三四十分钟,坐车只要一块五,他也舍不得花。
刚上高中时,何林烛学的是美术,期待考进艺校,成为一名美术工作者。但高三上到一半,他决定辍学打工。他仔细掂量了好久,认为自己最多只能考上专科,浪费钱不说,毕业了还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何林烛辍学后,带着仅有的两百块只身到成都闯荡。刚开始几天,何林烛白天找工作,晚上睡网吧。后来,他一天打三份工:送外卖、做家政、在KTV当服务员。每个月能挣七八千块,全都寄给母亲。
在KTV的工作最辛苦,身边的同事一拨接一拨地换,何林烛升上了主管。有时,他也会羡慕那些干了一个月就辞职的人,他也想像他们一样任性,但没办法。
何林烛手下的职员很多都是十几岁的小孩,看着他们,何林烛常想,如果弟弟还在,应该和他们差不多大,现在是在上学,还是已经像他们一样出来闯社会了呢?
何林烛回忆说,弟弟以前是孩子王,喜欢带着一帮小孩出门玩,每到饭点,妈妈总会让他去叫弟弟回家。
弟弟走后,只给家人留下了三张照片,分别由何林烛和父母保存。留在母亲那里的是弟弟六岁时一个人去照相馆拍的证件照。小男孩穿着橘色的外套,皮肤白净,单眼皮,招风耳,笑得羞涩,跟何林烛长得很像。
何林烛在成都待了一年半,便回到了新北川,他对着陆春桥的镜头说起回来的缘由:
“当时我在成都休假回来,我晓得我妈跟继父吵架了,当时看到我妈在那哭。我当时在想,他们如果再离婚的话,我妈在新北川只剩下一套房子和一条狗了,没有谁陪她。也是因为地震,我弟弟不在了,再加上我爸妈离异,当时我脑袋里就想,哪怕我在外面挣再多的钱,如果不能陪在她的身边,我挣那些钱也没什么意思。”
“我妈真的很不容易、很累,她是个女强人,我真的很佩服她。爱到深处是陪伴,我也觉得是情到深处了,我就真的离不开她了。”
当时,何林烛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始终都是笑着的。
回了新北川后,他继续送外卖、去KTV打工。也尝试过自己创业,开过一家叫“青春饭”的饭店,冬天卖板栗,夏天卖冰粉。“凡是能挣到钱的,都会试着干”。
我们的家庭与爱
十年过去,想起爸爸,母志雪更多的情绪是遗憾,遗憾他没能见证自己的成长。记忆中的父亲顶着一头卷发,高大帅气。小时候,她和弟弟总是缠着要爸爸背,在家门口的空地上跑来跑去。
地震前不久,十五岁的母志雪觉得自己的姓不好听,偷偷拽着妈妈到了派出所,想改姓。地震过后,母志雪再没动过改姓的念头,“姓氏是爸爸给我的,那是我们之间最好的连接”。
最开始,母志雪理解不了父母的感情,不明白真正的爱情到底是怎样的,直到遇见陈翔。“我当时耍朋友不是很认真,学校里的感情我不知道怎么去衡量。人要真的走到这一步,才理解我妈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2018年2月5日,母志雪和陈翔结婚了。婚礼前,母志雪带着陈翔一起去祭拜了她的父亲,陆春桥记录下了这一幕:
“在今后的生活中,永远都见不到他了,真的是很遗憾。工作、结婚、找到陈翔这样的人,我在想我爸要是看到陈翔这个样子,会不会满意啊?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你能多活过来一天,就一天,我给你讲讲我15岁到25岁这十年。”
在母志雪的婚礼上,母志雪的母亲把母志雪的手交到了陈翔手中,三人相拥。那一刻,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客人们都打开了手机的闪光灯,跟随音乐,缓慢地摇着。那是所有镜头中最打动陆春桥的瞬间。
2017年,何林烛也结婚了,妻子是在KTV认识的同事,一个活泼开朗的姑娘。今年4月,妻子又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他希望能养活一家人,过上稳定的生活。
何林烛辞掉了在KTV的工作,最近,他在绵阳学婚庆主持,计划回北川开一家婚庆公司。他还在左脚踝上文了一只小蜗牛。他觉得自己就是蜗牛,背着重重的壳,缓慢地爬着。但他不累,因为壳里住着他最爱的家人。
纪录片中,何林烛总结了他这些年的感悟:
“我觉得我们经历了地震的这一代人,跟外面没有这段经历的年轻人来比,我们更懂得生命的重要,特别是家,还有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责任。”
2018年初,陆春桥的拍摄进入了尾声。她似乎找到了答案,那些留在北川的同学大多数都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他们选择留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陪伴身边的家人。
陆春桥看到了母志雪对父母感情的感同身受、何林烛对家庭责任的重视。她想知道,自己的父母看到别的孩子都留了下来、陪在身边,自己的孩子在上海为梦想奔波,心里是怎么想的。
春节前夕,陆春桥为父母换上了羌族的民族服饰,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摆了一张椅子,母亲抱着狗,父亲一脸严肃。陆春桥躲在摄像机后面。
陆春桥问:像何林烛比较早在北川创业,留在他妈身边,母志雪很早就结了婚,我几个月不回来,你们有时候会不会难过?
母亲答:还是有哦,但是我又想,没关系,只要她过得好就得了,前途好。
父亲答:你说呢?肯定想,自己的女儿这么远,出门在外,儿行千里母担忧。
母亲眼泪落了下来:我要哭了,我不哭,我忍住。
父亲:是啊,不管你钱多钱少,一家人每天在一起,多巴适,多幸福。
母亲:你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们原来两个人,还年轻,跑得快,现在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只剩下了两个人,娃养大了不在家里了。特别是生病的时候,想着想着就觉得好造孽,这是我的心里话。
纪录片放映
12月16日下午,《初三四班》在北川电影院首映。
陆春桥刻意避开了那个特殊的日子,把日期定在了今年的末尾。“12月意味着一年的终点,对我们而言,也是上一个十年的终点”。
12月16日,首映仪式上,三位主角和他们的家人。受访者供图
班上的同学都回到了这座小县城。母志雪剪了一头短发,挽着丈夫和母亲,甜甜地笑。何林烛的宝宝成了焦点,孩子刚八个月大,挥着肉乎乎的小手,好奇的眼睛不住地眨。
看片子时,老北川的画面闪过,黄金城想到了自己的家,白色外墙,蓝玻璃。自己房间门口的柜子上,还摆着十四岁时的生日礼物,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水晶苹果和纸星星,全是初中同学送他的,地震后也没机会再拿出来。
弟弟的照片出现那一刻,何林烛没忍住掉了眼泪。
“很多年来,那场地震都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当地震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这些幸存者,无论是创业、工作,或者是结婚,我们都在努力地寻找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班真的很幸运,但幸好大家都在努力地不辜负这份幸运。我们这群人是特殊的,但也是普通的。经历了这场大地震活了下来,但是生活依旧还在继续,我们也要面对和你们一样的成长,也要在争吵和沉默后,最终学会理解父母,也要在努力工作后,懂得承担责任,也要在跌跌撞撞以后,遇到可以相互陪伴的人。”
片子的最后,是陆春桥的独白。
(感谢腾讯“谷雨计划”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新京报记者周小琪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张彦君
张海华
一群似鹭非鹭的大鸟,漫步于西双版纳的水田中,用它们的闭不拢的奇特鸟喙在水下探寻食物,专挑田螺这类别的鸟没法对付的“硬茬”来吃。这就是鼎鼎有名的钳嘴鹳。
5月初,我在西双版纳勐海县进行鸟类调查时,在当地坝子田野里,遇见大群钳嘴鹳。它们在秧田里悠然自得地觅食,与当地人和谐相处。
钳嘴鹳 本文均为 张海华 图
清晨的勐混坝子。“坝子”一词,在中国西南地区常可听到,意为山间的较大面积的平地。
“坝子”一词,在中国西南地区常可听到,意为山间较大面积的平地。与此相参照的名词,则是“梁子”,指的是山峰。
在勐海境内,有着版纳最高峰滑竹梁子,也分布着素有“版纳粮仓”之称的勐遮坝子与勐混坝子。
勐遮坝子遇“鹳河”
5月2日下午,我离开勐宋乡的滑竹梁子,经勐海县城,往勐遮镇驶去。
勐遮坝子是西双版纳州面积最大的坝子,广泛种植水稻。县里的冯主席告诉我,只要勐遮与勐混的稻子丰收,那么整个西双版纳州的粮食就够吃了。
那天下午3点多,车离开县城没多久,就进入了勐遮镇范围,公路两边全是平整的田地。我开得很慢,而且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要看到合适的环境,就停下来寻找水田里的鸟类。
快到著名的景真八角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忽见右边水田里有很多鹭鸟,还有不少钳嘴鹳。我赶紧就近停车,提了器材走过去。
田里的水很浅,碧蓝的天空与朵朵白云倒映其中。白鹭、牛背鹭、钳嘴鹳们都在分散觅食。见我走近,那些胆小的鹭鸟纷纷飞远,但没想到,它们的逃离引得原本并不怕人的钳嘴鹳也起飞了。
西双版纳勐遮的水田,碧蓝的天空与朵朵白云倒映其中。
钳嘴鹳在一座佛寺附近的田埂上站立休息,排列得相当整齐。
一只又一只巨大的鹳鸟掠过头顶,缓缓振翅,盘旋而上,越升越高。
奇怪的是,原本这田里只有二三十只钳嘴鹳,但当它们飞到高空后,不知从哪儿又飞来好多钳嘴鹳,于是至少有一两百只钳嘴鹳在飞。仰头看着这么多大鸟在天空御风而舞,心里十分激动。
以前,常听资深鸟友说无数迁徙的猛禽在高空飞翔,会出现难得一见的“鹰柱”(成群盘旋而上)、“鹰瀑”(成群飞下来)、 “鹰河”(成群滑翔而去)等壮观景象,从未见过这些的我,不禁悠然神往。没想到,如今我竟有幸见到了“鹳柱”和“鹳河”!
群飞的钳嘴鹳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钳嘴鹳。上次是2019年12月,在勐阿镇的温泉田里。钳嘴鹳是2006年10月才首次于中国被发现和记录的鸟类,因为栖息地和食物来源减少,现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低危等级。
成年钳嘴鹳的上喙基本平直,可下喙的中段却有明显的凹陷,以至于它的嘴就像一把夹核桃的钳子,当中留有明显的空隙。
钳嘴鹳最爱吃螺和蚌,如同铁钳一般的喙有利于弄碎或撬开螺蚌的硬壳,吃到里面鲜美的肉。
钳嘴鹳吃田螺。
钳嘴鹳
继续前行,路过一片荷塘,荷叶初生,水面上的动静一览无余。
一抬头,惊奇地见到一只黑翅鸢停在荷塘上空的电线上,它低着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水面。它企图捕食什么?我有点搞不懂,照理说水中的小动物并不在它的菜单上。它很警觉,很快发现了我,马上飞走了。
黑翅鸢
附近的电线上,停着一只头部偏红的伯劳。乍一看以为是牛头伯劳,可除了红色的头顶,其他特征都不像。奇怪,这是一种什么伯劳呢?回宁波后,请教了鸟友“七星剑”才确认,它是红尾伯劳。但这个亚种的红尾伯劳我以前没有见过。在华东,红尾伯劳是常见候鸟,我以前拍到过的两个亚种分别为灰头与褐头,但未见过红头的。
一只翅尖黑色的鸟掠过车头,飞落到左边的田野里。好像是灰头麦鸡!赶紧用望远镜一扫,果然见到三只灰头麦鸡。它们的保护色不错,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
灰头麦鸡的保护色很厉害,不仔细看发现不了它们。
曼瓦瀑布的野兰与小鸟
傍晚,来到勐遮镇上,看天色还早,我就到镇西看风景。勐遮坝子外围都是山,落日的余晖照在远处高山顶上的风车(风力发电机组)上,有一种神秘的美感。
5月3日早上,一走出旅馆,就见到一大群小白腰雨燕尖叫着掠过对面的楼顶。我原计划继续在附近田野中转悠找鸟,谁知,由于租来的车出了点问题,等解决后已快11点,我也没心思去田野里转了,寻思不如去附近的曼瓦瀑布找找鸟。
曼瓦瀑布是当地有名景点,位于勐遮镇西边的曼洪村曼瓦村民小组。2019年4月,我来参加勐海县自然与文化论坛时,曾跟着大家一起来参观过,当时拍到了黄颊山雀。
此番故地重游,心里还惦记着去年在瀑布入口处的大树上见到的兰花。因此,一到那里,就赶紧抬头寻找,果然见到一种,附生在离地不高的树杈上。可惜花期已到末尾,较大的一丛已开始萎谢,而较小的一丛还盛开着两朵花。花瓣洁白,先端为紫红色,十分艳丽。
我请教朋友周佳俊,得知这是杯鞘石斛。去年4月,我在附近大树上还拍到了一种开黄花的石斛,则是小黄花石斛。勐海就是这么神奇,稍微留意一下,就能见到各种稀奇的兰科植物。
杯鞘石斛
拾级上山,见瀑布的水量并不大,估计跟旱季降水较少有关。“居,居……”一阵音调很高的鸟叫声,透过瀑布喧闹的水声,清晰地传了过来。
这有点像红尾水鸲(音同“渠”)的鸣叫,但又不是很像。稍微等了一会儿,只见一只身体黑红色、头顶白色的小鸟从水雾中跳了出来,在湍急的水流旁的石壁上,灵巧地跳来跳去找吃的,果然是白顶溪鸲!
这种鸟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山区溪流中常见,在华东地区则分布较少。在宁波,迄今只有一笔记录。
曼瓦瀑布
白顶溪鸲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山区溪流中常见
小山不高,没走多久,就到了最高处的那一级瀑布,其落差约20米。飞泻而下的水流被岩石的棱角扯碎,在正午的阳光下扬起轻纱一般的水雾。
我在石上坐了一会儿,顿觉遍体生凉,十分舒适。偶然注意到对面石壁凹陷处有野花,过去一看,是一种报春花科的野花,粉紫色的,清秀可人。
下山途中,眼睛的余光瞥见一只小兽迅捷地跳过溪畔,消失在灌木丛里。我马上停住脚步,凝神在灌木中寻找。果然,看到它静静地伏在茂密的枝条之下。它有一个毛茸茸的大尾巴,体色以黄、黑、褐为主,背部毛色较深,体侧有黄黑相间的条纹。很快,它钻到了大石头的后面,再也不见了踪影。我回宁波后翻了半天《中国兽类图鉴》,也不能确认它是哪一种松鼠,只能说略似线松鼠。
松鼠消失的地方,有两只活泼的小鸟边飞边鸣,“唧唧,唧唧”,其声甜美而轻快。看得出来,这应该是快乐幸福的一对儿。它们不停地追逐嬉闹,终于有一个瞬间,居然同时停歇在我眼前的树枝上。看得清清楚楚,是一对方尾鹟(音同“翁”)。我以前没有拍到过这种鸟。
方尾鹟
它们羽色相近,只不过其中一只羽色稍深罢了,因此难辨雌雄。小家伙并不怕人,在我面前大大方方地“抓耳挠腮”,梳理羽毛。
方尾鹟身体亮黄,头部灰色,还有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属于不会认错的小鸟。跟其他的鹟一样,方尾鹟具有宽大的嘴基(张开嘴时,几成等边三角形),善于在飞行中捕食昆虫。方尾鹟在华东难得一见,属于匆匆路过的候鸟,而在云南,它们是留鸟。
勐混坝子:钳嘴鹳的“食堂”
离开曼瓦瀑布,回到勐遮镇上时已是下午3点多,肚中甚馁。在街边尝了一碗风味极为独特的“泰国凉拌”,然后直奔勐遮镇的另一个以风景优美出名的地方——勐邦水库,当地人称“天鹅湖”。
转了一圈,只见到小(音同“辟梯”)、棕背伯劳、白鹡鸰、白喉红臀鹎等常见鸟,估计在冬季这里的越冬水鸟会多一些。阵雨过后,阳光从云隙射出,照在湖畔的黄绿相间的秧田上,美得像一卷染过的画布。
勐邦水库及附近农田
此时手机响了,冯主席约我晚上去他亲戚家的山庄住,顺便去那里看鸟。离开水库,在山脚的田野的路边,忽见一只大杜鹃(即布谷鸟)停在眼前的电线上。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近距离的大杜鹃!它翩然起飞,还好又停在不远处。我赶紧停车,将它“收”入镜中。
大杜鹃
接上冯主席后,我们一起来到格朗和哈尼族乡和勐混镇交界处的山里,经阿鲁老寨、阿鲁新寨,来到山脊线上。停车远望,山的南边就是大片的田野,这便是勐混坝子。
空中有两只猛禽在盘旋,可惜飞得很高,拍下来后,只能大致认出是凤头蜂鹰和燕隼。当晚住在山庄里,山庄的庭院里有块巨石,从侧面看颇像大象。傍晚时分听到下面的森林中传来红原鸡雄鸟的响亮叫声,可惜找不到它。
5月4日,日出时分我和冯主席就起床了,再次驱车来到山脊线上。俯看南边,只见大半个勐混坝子都笼罩在洁白的云雾中,村寨、水田、道路,若隐若现,简直分不清这是天上还是人间。上午,山庄主人开车带我们去勐混坝子走了一圈,当时就看到了不少钳嘴鹳。
是日下午,我独自去那里的秧田拍鸟。上百只钳嘴鹳成小群分散在各处觅食,主要寻找田螺。劳作的村民来来往往,有时离钳嘴鹳不到十米远,它们也依旧不慌不忙地管自己找东西吃。看来,这些大鸟已经把当地人的粮仓也当作了自己的“食堂”。
傍晚,几十只钳嘴鹳在一座佛寺附近的田埂上站立休息,排列得相当整齐。除非有一只飞来的钳嘴鹳想要挤进来“插队”,它们彼此之间一般不会发生冲突。水田上空,有数以千计的黄蜻在飞,密度之高令人惊讶。有一只钳嘴鹳,迎着逐渐西落的太阳,尽力张开了翅膀,维持这个姿势几乎一动不动达数分钟。以前,我常见到善于潜水的鸬鹚有这种晾翅行为,没想到钳嘴鹳也会这么做。
水田边,晾翅的钳嘴鹳。
当天傍晚,我驱车前往布朗山乡。5日上午,我在布朗山的原始森林中拍鸟,算是探个路,计划以后再来。下午,在结束此次勐海鸟类调查、返回景洪市区之前,我又顺道拐到勐混坝子去拍钳嘴鹳,算是跟这些老朋友暂时告别。相信下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本文作者张海华系媒体人、博物作家,曾出版科普类作品《云中的风铃》、《夜遇记》等。联系我们/投稿邮箱:)
责任编辑:徐颖
校对:栾梦
- 热门文章
- 最近发表
- 标签列表
-
- 最新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