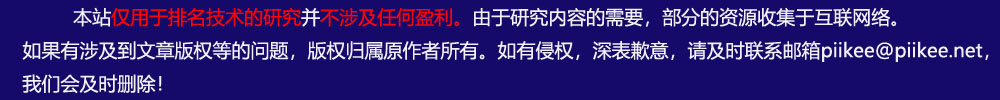antistress(antistress ag)
[闽南网]
抖音上最近又一款减压游戏非常火爆,这个游戏让我们按气泡、开车割草、挤牙膏,没有任何的难度,只是单纯的让我们减压,那么这款游戏叫什么呢,很多小伙伴不太清楚,小编带你详细的了解一下吧!
抖音减压的游戏名字
游戏名《antistress》
游戏的种类也是比较多,里面最受欢迎的可能就是按气泡、开车割草、挤牙膏,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游戏,大家都可以下载来自己感受下。
antistress玩法特色
1、里面各种各样的小物件
2、每一个玩法都不相同
3、点击手机进行趣味的移动、拖动玩法
4、同时有的还需要摇晃手机进行游戏
5、有效的减轻玩家的压力
好了,以上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抖音上很火的按气泡挤牙膏的游戏叫什么的相关资讯,希望能帮到大家!
第十七章 家庭与婚姻中的社交商
我的母亲从大学退休后,突然发现自己要守着一所空荡荡的大房子:她的孩子们都在其他城市生活,有些还相当远,而她的丈夫——我的父亲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现在回想起来,身为社会学教授的她当时做了一个相当明智的决定:她在家里留出一个房间,免费提供给所在大学的研究生们,而且优先考虑那些有着敬重老人传统的东亚国家的留学生。
现在她已经退休30多年了,这一做法还在持续。她的房客们一批一批地更换着,其中有些来自日本,有些来自中国。这些房客们似乎给她的健康带来了许多好处。其中有一对夫妻还带着一个孩子,这个小姑娘简直就把我母亲当作自己的亲奶奶。在她两岁的时候,她每天早晨都要跑到我母亲卧室里,去看看她是否已经起床了,而且每天都会拥抱我母亲好几次。
在她出生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快90岁了,她的出生使整栋房子都充满了快乐的气氛,我母亲好像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一下年轻了好几岁。我们无法知道母亲的长寿和她的生活环境究竟有多大关系,但是很多迹象都表明这种社交环境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随着老朋友的不断去世或者搬家,老年人的社交网络也在不断缩小。同时他们往往还会选择性地剪除自己的社交网络,只保留那些积极的人际关系。[1]这种策略会给他们的生理系统带来有益的影响。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我们的身体状况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脆弱。随着细胞的老化和死亡,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其他健康身体的防洪堤也在慢慢衰退。剪除那些无益的社交关系可以预防我们的情绪出现恶性波动。事实上,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在对生活美满的美国老年人进行调查后发现,社交网络给他们提供的情感支持越坚实,他们体内诸如氢化可的松之类的生理压力指标就越低。[2]
当然,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未必一定是最积极、最令人愉快的,比如某位亲人可能经常会使我们发狂,而不是让我们感到开心。不过,随着老人对次要社交关系的剔除,他们处理复杂情感(比如某个亲人所引发的酸甜苦辣)的能力似乎可以得到提高。[3]
一项研究发现,社交生活丰富、积极的老人所表现出来的认知能力的减退,要比那些孤立的老人晚7年。[4]
但是,孤独和老人们独自相处的时间并没有多大关系,和他们在某一天内与别人交往的次数也没有关系。事实上,老人们的孤独是由于缺少亲密、友好的交往而导致的。因此重要的是我们交往的质量:我们的交往对象是热情还是疏远,是支持我们还是打击我们。孤独的感觉(而不是单纯的朋友数量与交往次数)和我们的健康有着密切联系:人们的孤独感越强,他们的免疫系统和心血管功能往往就越脆弱。[5]
我们之所以要在年老的时候多关注自己的社交生活,还有另外一个生理上的原因。神经的形成,也就是大脑中神经细胞的生成,会一直持续到老年,当然速度会比年轻时要慢。许多神经学家认为,尽管这种速度的下降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单调的生活肯定会导致它的下降。新鲜事物在人们社交环境中的出现无疑会促进大脑对它们的学习,从而提高大脑中新细胞生成的速度。因此,许多神经学家正在和建筑师合作,希望研究出一种新型的养老院,使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与他人进行更多的交流,就像我母亲所采用的方法一样。[6]
保卫婚姻
当我走出小镇上的一个杂货店的时候,不经意间听到了坐在外面长椅上的两位老人的谈话。其中一位老人在询问他们所认识的一对夫妻最近的情况。
另外一个老人的回答很简洁:“你知道的,他们这辈子就争吵过一次——但是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这种人际关系引发的恶性情绪会对我们的身体状况产生不良影响。科学家们通过对新婚夫妇的研究发现了糟糕的婚姻关系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原因。这些新婚夫妇都认为自己的婚姻非常幸福,他们愿意将自己持续大约30分钟的解决分歧的情景用于研究。[7]在争论中,所检测的6类肾上腺皮质激素中有5类的含量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浓度的上升,这表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比较活跃。他们的血压也大幅上升,而且免疫系统的各项指标都出现了下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之后,免疫系统抵抗疾病的能力仍然会经历长时间的下降。他们争吵时的敌对态度越强烈,这种下降的幅度就越剧烈。科学家们总结说,内分泌系统“是一个把守人际关系与身体健康之间通道的重要大门”,它会释放压力荷尔蒙,从而影响心血管和免疫系统的功能。[8]当夫妻吵架时,他们的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都会遭殃,而且如果他们之间的战争长期持续下去的话,这种危害也会累加起来。
作为婚姻冲突研究的一部分,科学家们邀请了一些60多岁的老年夫妇(平均婚龄为42年)来到同一间实验室,以监测他们争吵时的情景。和新婚夫妇一样,争吵也使老年夫妇的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功能出现了下降,而且他们的怨恨越深,下降的幅度就越大。因为衰老本身会影响免疫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因此老年夫妇之间的敌意对健康产生的影响比新婚夫妇更加恶劣。在婚姻战争中,老年夫妇身体各项指标的下降程度比年轻夫妇更加严重,但是这种情况仅仅适用于妻子们。[9]
新婚妻子和步入老年的妻子都是如此。可以理解,那些在争吵中和争吵后免疫系统功能下降最严重的女性在一年之后对她们的婚姻状况也是最不满意的。
对于女性来说,如果丈夫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愤怒地冷落自己,她们的压力荷尔蒙水平就会上升。另一方面,如果丈夫在讨论的过程中表现出友善和同理心,那么他们的妻子就不会那么痛苦,她们的压力荷尔蒙也会相应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对于丈夫来说,不管解决分歧的过程是愉快还是痛苦,他们的免疫系统都不会发生多大变化。这种状况唯一的例外就是婚姻状况极度糟糕的人,这些人中丈夫和妻子的免疫功能都会比关系和睦的夫妻要弱一些。
许多方面的数据都表明,妻子比丈夫更容易因为恶劣的婚姻关系而导致身体健康状况的下降。但是总体来说,人际关系对于女性生理状况的影响并不比对男性的影响强烈。[10]
原因之一可能是女性比男性更加重视婚姻关系。[11]针对美国女性的许多研究都表明,良好的夫妻关系是她们幸福感产生的主要因素,而且会长期影响她们的身心健康。而对于美国男性来说,夫妻关系的重要性要低于个人成就感和独立性。
而且,女人天生的母性意味着她们会比男人更加关心自己亲人或朋友的状况,因此她们比男人更容易因为自己所爱之人的困境而感到痛苦。[12]除此之外,她们的情感更容易像坐过山车那样大起大落。[13]
科学家们还发现,妻子会比丈夫花更多的时间来反思不愉快的交往,而且她们的回忆会非常详尽、生动。当然,她们用于回忆美好时光的时间也多于丈夫。因为不愉快的记忆常常会不请自来,而且回忆某次冲突也会引发生理状态的变化,所以女性这种沉浸于苦恼中的倾向也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14]
综上所述,与亲人或者朋友之间产生的矛盾对女性身体的不良影响要远远高于男性。[15]例如,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发现,57群体中女性体内胆固醇的水平与她们婚姻生活中的压力直接相关,密切程度要远远高于男性。
一项对于充血性心力衰竭病人的研究表明,糟糕的夫妻关系导致女性提早去世的可能性要高于男性。[16]而且,女性在因为离婚或者亲人死亡等原因而遭遇情感压力时得心脏病的概率相当高,而引发男性心脏病的往往都是身体原因。在遭遇突然的情感打击,比如亲人的意外死亡等而引发压力荷尔蒙升高时,老年女性似乎也比老年男性更为脆弱,医生把这一状况叫作“心碎综合征”。[17]
女性身体对于人际关系起伏的敏感性初步回答了那个由来已久的科学疑问:为什么男性的身体状况会因为结婚而得到改善,而女性却不会。许多关于婚姻和健康的调查都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它仍然未必是正确的。使问题复杂化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缺乏科学的想象力。
一项历时13年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情景。在这项研究中,接近500名50多岁的已婚女性回答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对婚姻的满意程度如何?”结果非常清楚:女性对自己的婚姻越满意,她的健康状况就越好。[18]如果她与丈夫相处愉快,有共同的兴趣和相似的品位,沟通良好并且在财务等方面的意见一致,对性生活质量满意的话,这些情况都会通过她的生理指标反映出来。对婚姻感觉满意的女性的血压、葡萄糖和胆固醇水平都要低于那些婚姻不幸的女性。
其他的许多调查也都搜集了快乐或痛苦的妻子们的信息,尽管女性的生理系统对婚姻中的起伏更加敏感,但是关键问题还是她们婚姻的美满程度。如果在婚姻中的不幸多于快乐的话,她的身体就会遭殃。但是如果婚姻生活中的主旋律是幸福的话,她和丈夫的身体状况都会因此而受益。
拯救情感
一位女士躺在轮床上,被推进了核磁共振成像系统的一个人形洞中,周围都是机器,只留下几厘米的空隙。她听到巨大的电磁铁急速旋转的嘈杂声音,还瞥见在脸上方几厘米的地方有一个监视器。
每隔12秒钟,屏幕上就会闪过一系列彩色的几何图形,比如绿色的正方形、红色的三角形等。研究者们告诉她在屏幕上显示某个图形的时候,她就会遭到电击,电流虽然并不会引起疼痛,但是也会令人感觉不舒服。
有时候她需要独自承受痛苦,有时候会有陌生人握住她的手,还有些时候她的丈夫会伸出有力的大手握住她的手。
8位女性志愿者在理查德·戴维森的实验室中参与了这项实验,它的目的是评估在紧张、焦虑的时刻所爱之人对我们生理状况的缓解程度。结果显示,一位女士握住自己丈夫的手时比独自一人面对电击时的焦虑程度要低得多。[19]
握住陌生人的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她们的焦虑,尽管程度没有握住丈夫的手时那么强烈。值得注意的是,戴维森的研究小组还发现,想在女士们不知道手的主人是谁的情况下进行实验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实验中妻子们即使闭着眼睛也总是能够准确地分辨出自己丈夫和陌生人的手。
当妻子们独自一人面对电击时,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系统分析显示,她们大脑中的某些区域会活动,促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产生应激反应,使整个身体充满压力荷尔蒙。[20]如果威胁不是轻度电击而是来自他人,比如一个充满敌意的面试官,那么这些区域的反应会更加强烈。
丈夫有力的大手可以大大平复这一神经系统的躁动。这一实验填补了我们知识上的一项重要空白,它表明了人际关系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理系统,使其向着或好或坏的方向发展的。我们现在可以大体了解在情感拯救时大脑内的活动了。
另外一个发现也很重要:妻子对于婚姻的满意度越高,丈夫的大手给她的身体带来的益处就越大。这也解释了一个由来已久的难题:为什么有些女性的婚姻会威胁到她们的健康,而另外一些女性的健康则会因为婚姻而受益。
肌肤相亲会产生特别的抚慰效果,这是因为它可以引发催产激素,从而产生温暖的感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按摩或者温馨的拥抱会减轻人们的压力。催产激素的作用相当于压力荷尔蒙的“减压器”,它可以降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而这些神经系统的持续活动会威胁到我们的健康。[21]
当分泌催产激素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经历许多良性变化。[22]当我们进入轻松的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模式时血压会降低,而且新陈代谢也会从原来的应对压力的肌肉推进模式转变为复原模式,这时身体的能量会用于储存营养、生长以及康复。氢化可的松的水平会直线下降,表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活动正在降低。我们的疼痛极限也得到了提高,因此我们对于不适感的敏感性就降低了,甚至连伤口愈合的速度都会加快。
催产激素在大脑中的寿命很短,它在几分钟内就会消失。但是亲密、积极的长期人际关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催产激素分泌来源。每一次拥抱、友好的触摸和温馨时刻都会引发它的分泌。当催产激素持续分泌,比如我们与所爱之人共同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收获爱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持久益处了。催产激素使我们与所爱之人更加亲密,而且把这种亲密关系转化为良好的身体状况。[23]
让我们重新回到托尔斯泰夫妇的故事中。尽管他们在各自的日记中表现出了对对方的怨恨,但是他们毕竟生育了13个孩子。这么一个大家庭意味着他们的家中有着充裕的爱和被爱的机会。因此托尔斯泰夫妇不需要仅仅依靠对方,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情感拯救者。
积极的情绪传染
年仅41岁的安东尼·拉齐威尔奄奄一息地躺在纽约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内,他得的是纤维肿瘤,一种致命癌症。据他的妻子卡罗尔回忆,在丈夫生病的时候,他的表兄小约翰·F.肯尼迪曾经来医院探望过他。几个月之后,小肯尼迪也因为驾驶飞机在玛莎岛失事而去世了。
小肯尼迪刚刚结束聚会,还没有来得及换下晚礼服就走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医生告诉他安东尼只剩下几个小时的生命了。
小肯尼迪握住表弟的手,轻轻地唱起了《小熊泰迪的野餐》,这首歌是小肯尼迪的母亲杰奎琳在他们小时候经常为他们唱的摇篮曲。
已经奄奄一息的安东尼也跟着轻轻唱了起来。
用卡罗尔的话来说就是,小肯尼迪“使他进入了最安心的状态”。[24]
温柔的握手和摇篮曲无疑放松了安东尼最后时刻的情绪。人们的直觉认为,这似乎是帮助自己所爱之人的最好方式。
这一直觉已经得到了科学上的证实。心理学家发现,当人们在情感上越来越彼此依赖时,他们对彼此的生理状态也会起着积极的调节作用。这就意味着每个人从对方那里接收到的情感暗示都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特别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
处于和谐人际关系中的人们会帮助对方控制他们的痛苦情绪,就像关爱孩子的父母一样。当我们感觉痛苦或者不安的时候,我们的同伴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痛苦的根源,以便做出明智回应或者使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这些痛苦。这两种情况都会减轻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负面影响。
我们与所爱之人长期的分离会使我们丧失得到或者给予这种亲密帮助的机会。对他们的思念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人们对于这种对彼此生理系统有益的人际关系的渴望。在自己亲人或者爱人去世之后,情绪上的混乱无疑反映了人们这种虚拟自我的缺失。这种重要生理同盟的丧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配偶去世之后患病或者死亡的危险会大大提升。
男性和女性在这一过程中的反应各不相同。在压力状态下,女性大脑分泌的催产激素要多于男性。它会产生镇定的效果,促使女性去与他人交流,比如去照顾孩子或者和朋友聊天等。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谢利·泰勒发现,当女性在照顾别人或者与朋友交流的时候,她们的身体会分泌额外的催产激素,这会对她们产生进一步的镇定效果。[25]这种照顾和交流冲动似乎是女性所独有的。男性荷尔蒙会抑制催产激素所引发的镇定效果,而女性荷尔蒙则会促进这种效果。这种差别使得女性和男性在面对威胁时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女性会与别人交流,而男性则选择自己面对。比如,如果女性被告知她们将会遭到电击,她们会选择等待其他志愿者一起接受,而男性则愿意自己先来。男性似乎比女性更能够通过其他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物来平复自己的痛苦,电视或者啤酒都是不错的选择。
女性拥有的亲密朋友越多,她们身体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小,能够安享晚年的机会就越大。事实上科学家们发现,没有朋友对于女性健康的危害和吸烟以及肥胖等同样严重。即使在经历了严重的打击,比如配偶去世之后,有亲密朋友和知己的女性患上新的疾病或者丧失活力的可能性都比较小。
在与亲近的人相处时,我们控制情绪的能力,比如寻求安慰或者反思苦恼的能力,都会因为对方而得到加强。他们可能会提供建议或鼓励,或者通过积极的情绪传染来影响我们。这种与他人形成紧密生理连接的最初模式在婴儿早期与父母进行亲密交流时就形成了。这种大脑间的联系机制会陪伴我们一生,使我们的生理状态与我们所爱之人的生理状态密切相关。
心理学中用一个相当拗口的术语来表示这种二合一的状态:“相互调节的心理及生理单位”,它模糊了“我”和“你”、自己和别人的心理以及生理的通常界限。[26]这种亲密的人们之间界限的模糊使得他们可以进行双向的调节,影响彼此的身体状况。总之,我们不仅可以在心理上帮助(或者危害)别人,也会对他们的生理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你的敌视会使我的血压升高,同样,你的关爱也会使它降低。[27]
如果我们有一位亲密的伴侣、知心的朋友或者热心的亲戚可以依赖,我们就有了生理上的同盟。医学研究已经证实了人际关系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患有重病或者慢性病的病人可以因为情感上的抚慰而受益。因此,除了常规的药物治疗之外,生理同盟也是一剂良药。
亲密的情感是一剂良药
许多年前在印度乡下生活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当地医院一般都不为病人提供饭菜。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要一个病人住院,他的家人都会过来,在病房里搭地铺睡觉,还在病房里生火做饭,尽可能地照顾好病人。
当时我就想,生病的时候有亲人或者爱人日夜陪伴在身边,帮助驱除由于疾病而产生的低落情绪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这和西方社会中病人们的孤独情形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啊!
利用人际支持和关怀来提高病人生活质量的医疗体系也可以增强病人康复的能力。比如,病人躺在病床上等待第二天的一个大手术时难免会有些担心。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的强烈情绪往往会传染给其他人,而且人们越是紧张、脆弱,他们就会越敏感,感染别人情绪的可能性就越大。[28]因此,如果一个忧心忡忡的病人的室友也即将接受手术,那么他们两个人很可能会使彼此感觉更加焦虑和害怕。但是如果他的室友刚刚成功地接受完手术,因此感觉相对放松或者平静的话,那么室友的这种情绪就会使他感到安心一些。[29]
我曾经问过谢尔登·科恩(鼻病毒感染实验的领导者)是否有好的建议可以提供给住院的病人,他的建议是人们要有意识地寻找生理同盟。比如,他告诉我“去认识更多的朋友,特别是那些可以让你敞开心扉的朋友”是很有好处的。在我的一位朋友被诊断出患上了一种可能致命的癌症后,他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开始定期拜访精神治疗师,在自己和家人经历高度焦虑和痛苦的时候向他倾诉。
科恩告诉我:“关于人际关系和身体健康的最惊人发现就是:社交生活完整的人——那些已婚、与家人和朋友关系密切、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和宗教组织,并且经常参加社交活动的人,康复速度比较快,而且寿命也比较长。大约18项研究都证实了社交性和死亡率的密切联系。”
科恩说,多花些时间和精力去与那些可以使我们得到滋养的人相处,将有益于我们的健康。[30]他还鼓励病人尽可能地在生病期间减少与那些会对自己情绪产生不良影响的人交往,多与那些可以使自己感到心情愉悦的人相处。
科恩还建议,医院不应该只是教给心脏病患者如何避免疾病再次复发,而是应该考虑到病人的社交网络,培训那些最关心他们的人,使他们成为病人的生理同盟,共同改变必要的生活方式。
社交支持对于老人和病人非常重要,其他的一些因素却会妨碍他们实现对于温馨人际关系的渴望。其中一项就是家人和朋友面对病人时的手足无措和焦虑。特别是在病人的情况产生了不良的社交影响或者他们即将死亡的时候,周围原本亲近的人们可能会因为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过于焦虑而无法为他们提供帮助,甚至不再来看望他们。
曾因慢性疲劳综合征而卧床几个月的作家劳拉·希伦布兰德回忆说:“我周围的大部分人都疏远了我。”朋友们会互相打听她的情况,但是“在我收到一两张问候贺卡后他们就再没有了消息”。当她主动给老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他们的谈话总是会非常尴尬。挂断电话之后她感觉自己真傻,真不该打这个电话。
但是像所有遭受疾病折磨的人一样,希伦布兰德非常渴望交流,渴望与自己的生理同盟联系。就像谢尔登·科恩所说的那样,最新的科学发现“毫无疑问向病人的家人和朋友发出了一个信号,要求他们不要忽视或者孤立病人。即使你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他,至少也应该去探望他”。
这一建议向所有关心病人的人们表明,即使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拜访本身就是送给病人最好的礼物。拜访本身就会对病人产生惊人的影响,即使对于大脑严重受损,似乎毫无意识的植物人也是如此,医学术语把他们的这种状态称为“最低意识状态”。如果亲人或朋友向他们诉说往事或者轻轻地触摸他们,病人的大脑会和正常人的大脑产生同样的活动。[31]尽管他们似乎毫无反应,无法进行一次眼神交流,也无法回答一句话。
一个朋友告诉我她偶然读到一篇关于从昏迷中苏醒的人们的文章。这些人说,虽然他们当时一动也不能动,但是他们经常可以听到并且理解别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她正好是在去看望母亲的路上读到这篇文章的,她的母亲在充血性心力衰竭康复后也陷入了植物人状态。看到这一观点之后,她就不再只是静静地陪在母亲身边,看她的生命慢慢流逝,而是尽可能地去和她说话,或者轻轻地抚摩她。
亲密的情感在病人身体最脆弱的时候发挥的作用最显著,比如在人们患慢性病,或者免疫系统受损时,再或者年纪大了之后。尽管这种关爱并不是万能药,但是最新数据表明它有时的确可以改变人们的生理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讲,爱不仅可以改善病人的心境,而且还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同药物治疗一样的效果。
因此,内科医生马克·佩特斯极力主张我们应该学会辨认表明病人渴望人际关系的微妙信号,比如“眼泪、微笑、眼神甚至沉默”等,并且做出敏锐的回应。
佩特斯年幼的儿子在住院接受手术之前非常惊恐害怕、烦恼不已,而且因为发育迟缓,他当时还不会开口讲话,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32]手术结束之后他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胳膊上在进行静脉注射,一根管子通过鼻孔插进胃部,鼻孔中还有氧气管,还有一根管子把麻醉剂输送到椎管,另外一个管子通过阴茎到达膀胱。
佩特斯和妻子看到心爱的儿子这副模样心如刀绞,但是他们从儿子的眼神中感觉到自己可以通过爱意来帮助他,比如抚摩他、深情地望着他,或者仅仅在旁边看着他,什么都不做。
就像佩特斯所说的那样:“爱,就是我们的语言。”
[1]On choosing pleasant relationships, see Robert W. Levenson et al., “The Influence of Age and Gender on Affect, Physiology,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A Study of Long-Term Marriag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no. 1(1994), pp. 56–68.
[2]On emotional support and biological stress, see Teresa Seeman et al., “Social Ties and Support and Neuroendocrine Function,” MacArthur Studies of Successful Aging,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6 (1994), pp. 95–106. Earlier studies have found the same relationship, emotional support lowering risk, with a range of other biological measures, including lower heart rate and blood pressure, lower serum cholesterol, and lower norepinephrine: Teresa Seeman, “How Do Others Get Under Our Skin?” in Carol Ryff and Burton Singer, eds., Emotio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On older people and emotional complexity, see L. L. Carstensen et al.,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Everyday Life Across the Lifesp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2000), pp. 644–55.
[4]On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and cognitive ability in the elderly, see Teresa E. Seeman et al., “Social Relationships, Social Support, and Patterns of Cognitive Aging in Healthy, High-functioning Older Adults,” Health Psychology 4 (2001), pp. 243–55.
[5]On loneliness and health, see Sarah Pressman et al., “Loneliness, Social Network Size, and Immune Response to Influenza Vaccination in College Freshmen,” Health Psychology 24 (2005), pp. 297–306.
[6]On social engineering in homes for the elderly speeding neurogenesis, see Fred Gage, “Neuroplastic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welfth meeting of the Mind and Life Institute, Dharamsala, India, October 18–22, 2004.
[7]On newlyweds disagreeing, see Janice Kiecolt-Glaser et al., “Marital Stress: Immunologic, Neuroendocrine, and Autonomic Correlate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840 (1999), pp. 656–63.
[8]Ibid., p. 657.
[9]There was lit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rbal struggle and endocrine measures in the older husbands.
[10]Tor Wagner and Kevin Ochsner, “Sex Differences in the Emotional Brain,” Neuro-Report 16 (2005), pp. 85–87.
[11]On the importance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see Carol Ryff et al., “Elective Affinities and Uninvited Agonies: Mapping Emotion with Significant Others Onto Health,” in Ryff and Singer, Emotion, Social Relationships. From middle age onward men plac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n their relationships, but still to a lesser extent than women.
[12]On women and caring, see R. C. Kessler et al., “The Costs of Caring: A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I. G. Sarason and B. R. Sarason, eds., Social Suppor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5), pp. 491–507.
[13]On women being more sensitive, see M. Corriel and S. Cohen, “Concordance in the Face of a Stressful Ev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1995), pp. 289–99.
[14]On memories and biological shifts, see Kiecolt-Glaser et al., “Marital Stress.”
[15]Numerous studies find that women show stronger immune, endocrine, and cardiovascular reactions to marital arguments than do their husbands. See, for example, Janice Kiecolt-Glaser et al., “Marital Conflict in Older Adults: Endocrinological and Immunological Correlate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9 (1997), pp. 339–49; T. J. Mayne et al.,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Acute Marital Distress on Emotional, Physiological and Immune Functions in Maritally Distressed Men and Women,” Psychology and Health 12 (1997), pp. 277–88; T. W. Smith et al., “Agency, Communion, and Cardiovascular Reactivity During Marital Interaction,” Health Psychology 17 (1998), pp. 537–45.
[16]On women’s deaths from heart disease, see James Coyne et al., “Prognostic Importance of Marital Quality for Survival of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88 (2001), pp. 526–29.
[17]On broken heart syndrome, see Ilan Wittstein et al., “Neurohumoral Features of Myocardial Stunning Due to Sudden Emotional Stres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2 (2005), pp. 539–48.
[18]On satisfaction and women’s health, see Linda Gallo et al., “Marital Status and Quality in Middle-aged Women: Associations with Levels and Trajectories of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Health Psychology 22, no. 5 (2003), pp. 453–63.
[19]On holding hands, see J. A. Coan et al., “Spouse, But Not Stranger, Hand Holding Attenuates Activation in Neural Systems Underlying Response to Threat,” Psychophysiology 42 (2005), p. S44, J.A. Coan et al., “Lending a Hand: Social Regulation of the Neural Response to Threa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in press.
[20]The circuitry encompasses the insula, hypothalamus, right prefrontal cortex, and anterior cingulate.
[21]On neuroendocrinology and oxytocin, see C. Sue Carter, “Neuroendocrin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Attachment and Love,” Psychoneuroimmunology 23 (1998), pp. 779–818. The data for the health benefits of oxytocin are strong, but in map-ping biological impacts of relationships, researchers will undoubtedly find that other neuroendocrine pathways are also involved in the mix.
[22]On the health benefits, see Kerstin Uvn-Moberg, “Oxytocin Linked Antistress Effects: The Relaxation and Growth Responses,” Acta Physiologica Scandanavica 161 (1997), pp. 38–42. While oxytocin has a short half-life—a matter of minutes—it seems to trigger a cascade of secondary mechanisms that have broad health advantages.
[23]On blood pressure and oxytocin, see ibid.
[24]Carole Radziwill, What Remains: A Memoir of Fate, Friendship, and Love (New York: Scribner’s, 2005).
[25]On women and stress, see Shelley E. Taylor et al., “Female Responses to Stress: Tendand- Befriend, not Fight-or-Fligh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7 (2000), pp. 411–29. See also Shelley E. Taylor, The Tending Instinct (New York: Times Books, 2002).
[26]On relationships as emotional regulators, see Lisa Diamond and Lisa Aspinwall, “Emotion Regula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Emphasizing Self-regulation, Positive Affect, and Dyadic Processe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7, no. 2 (2003), pp. 125–56.
[27]Some argue that our overall pattern of cardiovascular and neuroendocrine activity varies to a significant degree as a function of the emotional status of our most major relationships. See, for example, John Cacioppo, “Social Neuroscience: Autonomic, Neuroendocrine, and Immune Responses to Stress,” Psychophysiology 31 (1994), pp. 113–28.
[28]On stress and contagion, see Brooks Gump and James Kulik, “Stress, Affiliation, and Emotional Contag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 no. 2 (1997), pp. 305–19.
[29]On patients and surgery, see James Kulik et al., “Stress and Affiliation: Hospital Roommate Effects on Preoperative Anxie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Health Psychology 12 (1993), pp. 118–24.
[30]In this sense, the network of people who deeply care about a patient’s well-being is an underutilized health resource.
[31]On brain activity in minimally conscious patients, see N. D. Schiff et al., “fMRI Reveals Large-scale Network Activation in Minimally Conscious Patients,” Neurology 64 (2005), pp. 514–23.
[32]Mark Pettus, The Savvy Patient (Richmond, Va.: Capital Books, 2004).
- 热门文章
- 最近发表
- 标签列表
-
- 最新留言
-